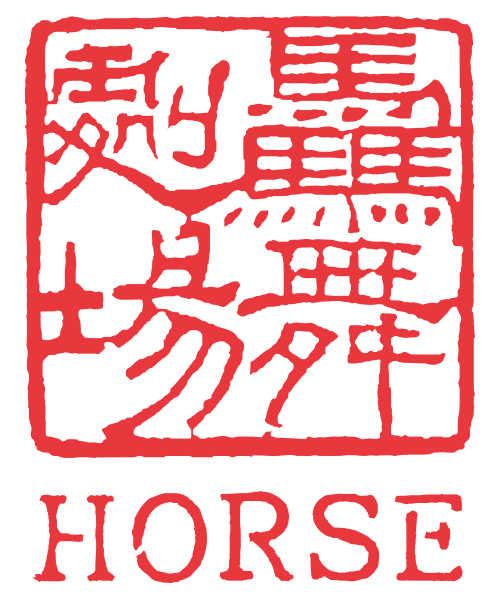驫舞阿凱Archiving計畫─續航二黃雯
-
訪談|陳柏潔
整理撰稿|余岱融
「驫舞阿凱Archiving計畫──續航」延續自驫舞劇場2020年開啟的檔案計畫,將目光從核心藝術家身上,轉向聚焦舞團近二十年來,幾位深入合作的藝術行政與製作人。他們是演出掌聲後方的另一組人馬,掌握不同地區的政治與文化,將創作概念落實為文字與數字,將藝術語彙轉化為溝通與推廣的語言。他們要了解人情世故,也要能把結案、送案日期倒背如流,轉身還要處理被汗水浸溼的演出服,和變化多端的便當名單。
驫舞劇場的行政編制隨舞團成長經歷許多不同階段,這次「續航」,邀請四位夥伴共乘:莊增榮、黃雯、葉名樺與鄢繼嬪。除了從他們眼中回顧、梳理舞團駛過的航道、看過的風景,也試圖從個人史以及他們與舞團的互動中,探詢臺灣2000年後的藝文生態與文化政策,如何反應在組織與藝術行政個人身上。本計畫依訪談對象,刊出四篇檔案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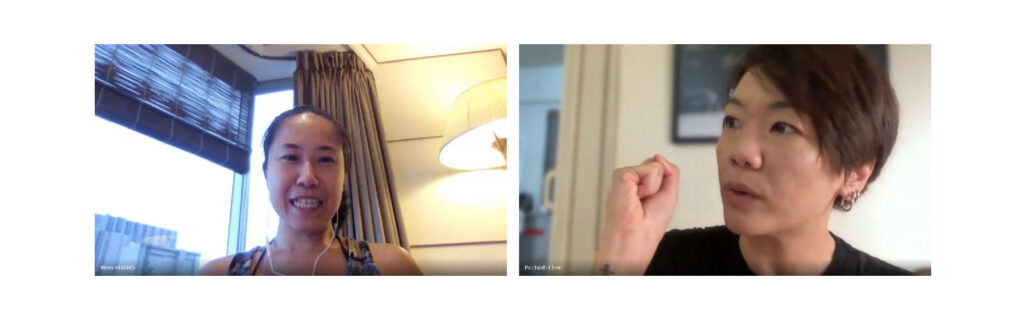
驫舞阿凱.續航之二:黃雯
2010 黃雯加入驫舞劇場,擔任舞團經理。舞團開始每年推出兩檔製作,其中一檔為支持團內舞者發表創作的平台,同年,舞團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補助
2011 驫舞劇場於華山1914文創園區發表橫跨展覽、聲音、表演之跨國作品《繼承者》
2012 驫舞劇場與林奕華合作《兩男關係》
2013 黃雯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國際大學攻讀藝術文化管理碩士
2014-2017 黃雯於國藝會平台「Fly Global 台灣數位表演藝術國際續航計畫」任職,擔任專案經理
2017- 蘇威嘉發表《自由步──身體的眾生相》,黃雯回歸團隊擔任製作人。其後與團隊共同開啟的計畫包括:舞蹈結合AR技術之「看見你的自由步」系列作品、國際跨界製作《半身相》等。亦與製作人夏曼青共同進行疫情期間的線上計畫,如《14》、「2021樹林跳:跳島舞蹈節」等。
2018-2021 黃雯於國藝會「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任職,擔任專案經理
2019-2020 黃雯於臺南藝術節擔任策展團隊製作人
一、誤打誤撞、仍有跡可循的藝術行政之路
大學就讀外交系的黃雯,自認生長背景和表演藝術並沒有太多緊密的交會。雖說她不曾於任何階段,接受過藝術科班訓練,但或許因為小時候學過爵士舞,媽媽會帶她去看各種演出,自己大學時也會買票進劇場,因此對表演藝術並不算陌生。從沒想過會進入劇場圈工作的黃雯,回想起大學打工的咖啡廳牆上一張無垢舞蹈劇場(後簡稱無垢)《花神祭》的海報,成為她日後進入表演藝術領域的濫觴。
大學畢業後,黃雯曾在活動公關公司任職約半年,但逐漸意識到,對自己而言那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工作環境。上網搜尋工作機會時,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後簡稱國藝會)的網站上看到一份藝術行政職缺,正是來自那張被自己從咖啡廳帶回家、貼在房間海報的舞團。她在無垢工作的五年間,頭兩年擔任全職行政,後三年負責演出製作專案。由於該團作品的製作期程都很長,擔任專案人員也幾近等同於一個全職工作。2009年離開無垢後,黃雯以獨立工作者的身分接案,隔年夏天和好友在歐洲旅行了一個月後,決定重回正職的生活。
黃雯表示,雖然已經有五年的工作經歷,但那段時間尚未掌握臺灣舞蹈或表演藝術的生態,當時也不太認識中小型表演團隊,同時,自己和同行之間除了業務上的需求,並沒有太多交流,大家也都傾向相敬如賓,各自努力。倒是因為在無垢的經歷,為她奠定了藝術行政上看似傳統、但仍然受用的工作知識與倫理基礎。她承認在獲知驫舞劇場要徵才時,並不太了解這個團隊,也不曾看過他們的演出。由於當時住在板橋,有地緣因素,就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順利進入了驫。
二、初入驫舞劇場,學習與中小型藝術團隊工作
黃雯於2010年加入驫的團隊,接手前任舞團經理莊增榮的職務,當時舞團還有另一位行政同仁楊喆甯。黃雯認為,雖然從職稱上看來,她比較像是一名主管,但在工作關係上,兩人其實相當平行。相較於無垢,黃雯在驫舞劇場負責更多財務管理的工作,也是她首次著手一個表演藝術團隊的財務規劃。黃雯表示,由於驫最初是由團隊成員共同出資所創,財務自然有一定的透明度。而本以為自己對數字不太擅長,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她卻發現逐漸能夠透析財務報表的訊息、掌握其中端倪,也對這份工作產生更多興趣。
加入驫舞劇場的第一年,是黃雯口中和團隊高強度的磨合期。由於與過去大型舞團的工作模式不同,當時驫的行政流程更為彈性,但有時也意味著更加模糊,甚至有些混亂。許多黃雯過去熟悉的操作方法,在當年驫的身上似乎起不了功能。加上驫舞劇場自創團以來就常使用共同創作的方法,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也難免有多頭馬車的狀況出現。例如:黃雯加入舞團後的第一個製作,是2010年兩廳院舞蹈秋天的委託作品《我》,除了陳武康和蘇威嘉兩位核心藝術家,還包括受邀加入的團外創作者:蔡柏璋、黃健瑋。如何聆聽、了解眾多創作者的想法與需求,黃雯認為是十分挑戰之處。此外,對於製作上「錢該怎麼用」,藝術創作面與行政管理面也時常也有不同意見交鋒。
「早期驫舞劇場的演出沒有舞監,例如記者會時,前台要自己跑到劇場內問:『現在能不能放觀眾了?』」
也在這個階段,黃雯開始接觸到更多業界同行。在舞團辦公室和排練場,除了不同製作合作的藝術家外,也不時有武康和威嘉的學弟妹或學長姐會來串門子,認識越來越多不同的臺灣舞者和編舞家。另外,她也開始參與業界舉辦的講座或論壇,但主要以吸收知識為主,並沒有特意為了社交或為職涯發展鋪路。而在國際交流的部分,當時驫舞劇場已經有許多國際巡演的經驗,包括2009年獲得台新藝術獎的《速度》,以及2012年的《兩男關係》,陸續受到國際場館和藝術節邀演。她坦言在那個時候,自己和舞團都比較專注於「單點進出」,也就是如何讓作品可以從一個地方賣到下一個地方,還沒有國際平台、國際交流的概念,當時臺灣也比較缺乏這方面的資訊。

2010年兩廳院舞蹈秋天的委託作品《我》,除了陳武康和蘇威嘉兩位核心藝術家、年輕舞者張子凌,還包括受邀加入的團外創作者:蔡柏璋、黃健瑋
2012年《兩男關係》為驫舞劇場最具帶表性作品之一,關於陳武康和蘇威嘉真實的情誼
回想2013離開台灣、也離開驫,到西班牙唸書前,黃雯表示自己花了一段時間規劃,讓驫的行政團隊可以在她離開後順暢地運作下去。當時除了包含黃雯在內的三名正職行政外,葉名樺也開始陸續分擔一些行政事務,例如當時部分仍在執行中的國際演出案。黃雯曾告訴名樺:「這些後續國際關係的維繫,只能交給一位不會離開的人,那個人就是你」。而在舞團財務上,也因為舞團經理的職務,讓黃雯覺得自己有更多責任,把當時已經建立好的小制度延續下去,並且讓舞團的管理從手上交出去時,至少是損益兩平、能夠繼續前行的狀態。
三、出國求學,與參與國際交流平台的開始
黃雯在2012年卸下舞團經理的職務,後續以專案合作的方式,直到隔年出國進修。她表示,其實在無垢任職時,進修的念頭就已經放在心裡了,延宕了幾年也終於實行。出國學習期間,腦袋總有許多小火花併發,但一直到一年的求學結束後,才把這些小火花串聯在一起。當時她對一個藝術節如何帶起城鎮發展,以及藝術如何進入住民日常生活很感興趣。因而以地景藝術及城市/鄉鎮藝術節為題,申請了國藝會的「海外藝遊」專案,觀摩不同的案例如何將藝術、環境與經濟結合在一起。黃雯對於藝術與城鎮空間關係的興趣,後續也落實在她擔任2019年臺南藝術節策畫團隊製作人的工作成果中。
2014年回臺後,黃雯首先接下廣藝基金會「QA Ring」計畫,該計畫由周東彥和吳宗祐主持,主要針對科技跨表演藝術的領域,尋找能為臺灣藝術家提出指引與建議的國際導師。黃雯回想,廣藝基金會的計畫,也反映了當時臺灣表演藝術圈開始重視「平台」的功能與可能。她後續也加入國藝會於2014年底成立的「Fly Global 台灣數位表演藝術國際續航計畫」,和獨立製作人出身的計畫主持人孫平一起工作,以拓展、建立「網絡」為方法,支持臺灣數位與科技表演藝術在國際的發展。相較於出國前,黃雯表示自己在這個工作期間,認識了更多的作品、團隊、藝術家,以及相關機構、場館和藝術節,也才在實踐的過程中,建立過去所沒有的國際網絡和交流觀念,讓累積的工作知識與經驗能有所轉化。
在Fly Global平台工作了三年,黃雯回憶當時因為屬於中介者的角色,自己在大部分的合作案中都只是牽線的媒人,後續製作或計畫執行上的迫切性往往與自身工作無關。到了第三年,這種有一份正職工作、卻總是「懸在空中」的感受也越發強烈。事後回想,黃雯認為自己當時因為這種懸置狀態帶來了某種安逸,讓自己在工作上少了即時的「危機意識」。因此,主持人孫平便建議她轉為兼職身分,好讓她有機會重新投入製作工作。
四、二進驫舞劇場,製作人身分的開展,經理身分的延續
也剛好在這個時刻,武康和名樺在與黃雯談天時獲知,她在國藝會平台的專案工作即將轉為兼職,邀請她以專案工作的方式重回驫的團隊,再續前緣。黃雯回想,當時雙方對於工作內容、職稱其實有做過一番討論。她認為2010到2012年在驫的期間,其實是一段漫長的磨合期。回顧當時,雖有企圖建立一些小制度,但整體而言,並沒有完成所謂的工作方法或行政體制,對於自己要重回驫的職務定位,也多有遲疑。最後,雙方同意以專案製作人的身分,重啟合作。
黃雯承認,在這之前不太敢叫自己「製作人」,過去總覺得是極為資深、能夠找到大量資源挹注的藝術行政,才有資格被稱為製作人。當時臺灣對於製作人在藝術面與行政面的工作內容與角色,也開始有比較清楚的討論,她也想嘗試看看「當一名製作人」究竟是甚麼狀態。
黃雯坦言:2017年回團的第一個製作《自由步──身體的眾生相》中,她著手的主要還是財務控管,在選角、編舞構想與劇場設計等方面,並沒有太多參與空間,因此仍偏向執行製作或製作經理的角色。一直要到2018年《半身相》和2020年《看見你的自由步》時,她才有機會在製作最初期,和藝術家從創作、製作概念討論起,包括規劃不同階段的資源挹注,或是就合作對象交換意見。她認為,無論是跟武康還是威嘉,彼此都在這些過程中一起學習如何跟「製作人」這個角色一起工作,也成就彼此現在良好的默契基礎。


2018年《半身相》從日本城崎國際藝術中心駐館排練到2019年泰國象劇場巡演製作會
黃雯也承認,2010年首次進入驫的行政團隊期間,她對團隊藝術家的創作並沒有太深刻的感覺。倒是2014年自西班牙求學回國後,純粹以觀眾身分前欣賞了武康在國家戲劇院演出的作品《裝死》,發現自己終於「看懂了」這位藝術家。她表示:雖然對某些藝術行政工作者而言,藝術家的創作會大大影響合作意願,但很多時候也要理解,藝術家或許也在嘗試自身創作風格與語彙的路上。離開了出國前那個比較急躁的自己,回歸驫舞劇場的黃雯認為自己比當年有著更好的立基點,與舞團繼續合作。
2017年重回舞團時,黃雯觀察到武康與威嘉已經分別各自展開創作計畫,因此多項專案同時進行也成為常態。雖然最初是以專案製作人的角色回歸,她還是試圖在管理上建立更精簡的流程和橫向溝通,例如具體落實每週例會、會議記錄與工作進度追蹤,也建立專案工作的表格工具,讓所有專案進度都能被團隊成員掌握。
「隨著藝術家結婚、生小孩,他們也開始要對自己的私人財務更有概念,這可能也是跟團隊財務管理相關的其中一個轉捩點。」
精進管理工作上的需求,也來自黃雯發現她於2014到2017年離團的幾年間,團隊管理狀態的不穩定。其中包括行政團隊組成歷經多次變動,有時可能是完全沒有藝術行政經驗的新鮮人,有時是交接不完整,導致資料有所缺漏。而在財務面,從2013年她離開時仍有結餘,到2017年回團時又呈現相當程度的虧損。這些現象也都間接讓黃雯除了原本談定的專案製作人職務,又重新拾起了舞團經理的身分。因此這次回團後,黃雯除了嘗試和藝術家共同學習、培養製作上的工作方法,也開始半邀請半逼迫武康、威嘉一起檢視製作的財務報表細節,也從過去的「財務透明」(大家都能看到報表),到現在的「透明財務管理」(一起討論錢怎麼花)。在這個過程中,製作人和藝術家共同協調各個計畫中不同項目的資金如何運用,以及每個專案要攤提多少比例,投入舞團的固定營運資金中。

《自由步──身體的眾生相》

《自由步──一盞燈的景身》
《FREESTEPS 自由步》是驫舞劇場蘇威嘉從2011年起自行展開的舞步探索計劃,這個探索計劃的概念是以身體的動(舞步)作為出發,試圖創造各種被觀賞時可提供的想像。
五、驫舞劇場行政團隊的歷程與轉變
回顧驫舞劇場的行政團隊發展,黃雯認為在2010到2012年間,舞團從過去共同創作,擴展到邀請戲劇、聲響、視覺裝置的表演者與藝術家成為核心創作者,藝術行政也需要在短時間內,學習與不同藝術背景的夥伴溝通與合作。而因應不同的製作規模,例如《繼承者》設定在大型場地進行展覽和演出,如何租借合適的硬體空間讓製作逐步落實,是當時行政工作的挑戰。這個階段因為創作者的意念常快速換軌,行政也常要打帶跑,往前追趕,盡速為製作鋪出前方的軌道。一旦回到較為慣常的創作規格,例如《兩男關係》,行政團隊在宣傳、行銷等各個環節上就更有餘裕發揮,支持製作前進。
2013到2016年間,雖然不在團隊,但黃雯從側面觀察發現,驫的作品從共同創作轉為更集中在單一編舞家的意志,也持續支持年輕編舞家如黃懷德、劉冠詳的作品。就演出形式來看,大致延續過去的方法,藝術行政並沒有面臨太多規格上的挑戰。但由於行政人員流動頻繁,相關製作經驗如何累積在舞團中,還有待商榷。


驫的行政工作團隊工作環境從辦公室到排練場
黃雯於2017年回歸舞團後,武康與威嘉的創作路線越趨明確,製作與行政工作更具焦於如何維繫藝術家創作思考的空間。加上舞團的藝術實踐類型,從演出製作拓展到藝術節策劃以及推廣活動,專職的行政夥伴要如何分攤這些工作,也是不同於以往的現象。因此舞團也逐漸增聘行政人員,從過去大多為兩名專職行政,在2017年後逐步轉為三名正職搭配兩到三名兼職及專案人員。行政夥伴從過去「一視同仁」的打帶跑狀態,轉變為針對個人特質和團隊組成進行分工。2019年開始,舞團有了專職的財務管理人員,2021年起,武康與威嘉則有各自的排練助理,協助掌握製作和專案工作的進行。
黃雯坦言,現階段兼職人員在行政團隊中的比例很高,是一種策略性的風險分攤。由於正職的藝術行政工作往往相當消耗,若團隊中都是正職行政,一旦一名行政離職,就會立刻加重其他同仁的工作負擔,很容易產生離職連鎖效應。因此目前的規劃,是將舞團日常庶務與營運工作,分配給長期固定合作的兼職同仁,有些是舞團持續合作的舞者,有些是有具良好關係與合作默契的行政夥伴,專職人員主要負責各項專案工作。
在中小型舞團的架構下,很難有所謂「人力資源」的部門,因此驫的人力招募還是由舞團核心成員共同執行。目前每年度的工作職務與分配由黃雯負責,她和名樺則分別監督不同專案的工作進度。此外,在薪資的部分,舞團每年固定加薪3%,以抵抗貨幣通膨的趨勢,若有針對特定同仁有更高的加薪比例,同樣會回到核心成員共同討論。在勞動條件上,除了勞健保,還有幫同仁加保額外的「大補帖」保險項目,以及提供年度健康檢查。黃雯表示,雖然在福利制度上不到完整,但現階段算是盡其可能了。
近年舞團除了持續發表製作,也策劃像跳島舞蹈節、回溯臺灣舞蹈環境發展的「重製場」等活動,當然也需要行政的參與與支援。黃雯表示,隨著這些策劃專案的形成,團隊內部需要就藝文生態環境的議題進行更多溝通與討論。例如她常常會分享講座、評論甚至展覽的資訊,讓同仁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功課。她認為,這些材料除了用來提升藝術行政的知能,也是要讓大家理解「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因為只有在工作實踐中找到意義,才會有意願繼續一起做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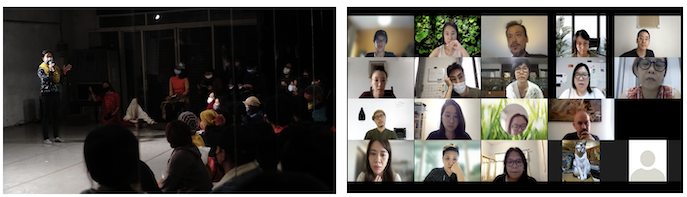
2021《2男抬槓》作品發展呈現前黃雯與觀眾分享
2021《14》疫情中發展的跨國連線直播行政團隊與國際藝術家線上會議
六、從製作人的角度,看驫的藝術實踐
談到自己和藝術家的工作狀態,黃雯直言是一種「隊友」的關係。因此,既不是過去藝術行政要「服務」藝術家的觀念,雙方也不是「朋友」的身分,而是彼此學習、討論、支持和共同前行的關係。黃雯表示,藝術面和行政面一定是相輔相成,自己過去在平台工作中累積的國際連結和合作可能,還是要在藝術家和製作身上才能落實。而驫的兩位藝術家,也都有一定開放度和冒險態度,讓她有空間去嘗試。因此從舞團外部來看,好像時常是由黃雯主導發展方向,但實際上,並沒有誰擁有唯一的話語權或控制權,基本上仍舊是彼此共同討論出的結果。
黃雯也表示,和成團初期直接把自己的積蓄作為舞團發展基金相比,兩位核心藝術家現在對於如何尋找資源有相當完整的認識,很多時候,也會跟著獎補助的方向來思考要開展甚麼計畫。黃雯坦言,身為一名製作人,創作上最初的熱情、創意與概念的原點,對她而言相當重要。通常她偏向先理解這些部分,再去尋找合適的資源。她表示,在臺灣現階段的藝文環境與補助政策下,表演團隊營運的確時常需要尋求補助的支持,並在補助標準與方向中進一步思考自己要做什麼。目前驫舞劇場的團隊業務包括委託創作、補助申請、合作案等,其中在補助申請的部分,約有八成是跟著補助辦法來規劃的。對黃雯而言,她也希望在這個背景下,能有更多空間來思考開展計畫的初衷。
不過黃雯也表示,驫舞劇場近年的舞團檔案建置與推廣活動,其實都來自團隊成員共同的關注和興趣,加上自己也逐漸遠離充滿青春活力的年紀,因此也會思考:身為一名觀眾,未來邁入老年時的可能需求。例如「重製場」是武康想要知道自己如何從過去的舞蹈教育中,轉變成現在的狀態,因此有了一系列對於臺灣舞蹈生態的回溯。跳島舞蹈節則是想要讓舞蹈更好玩、有趣,和威嘉的樂齡舞蹈工作坊有著類似的起心動念。反觀創作上,運用AR技術的《看見你的自由步》,來自威嘉長期對於影像的偏愛與好奇。黃雯認為,在那些藝術家有著飽滿初衷的計畫裡,他們自己也會獲得更多創作的樂趣。
「我覺得驫做舞團檔案或是重製場、大眾推廣工作坊,都算是在回應整個藝文環境。」
在近年的合作中,團隊內也會就不同的「開源」可能性進行討論,例如一些資源較豐沛的合作案。比起委託的藝術創作,這樣的專案通常更偏向活動策劃。黃雯坦言,武康和威嘉基本上都會蠻願意接受這樣的邀請,對於更大規模的發展也有野心,但回到自己身上,她還是會考慮以團隊目前的行政量能以及自己的心力而言,是否接得下這些任務。偶爾在製作案中,也會遇到需要回應獎補助或委託機制的時刻,這時如果藝術家願意處理如何貼近「標準」,她也願意退一步,回到盤點製作、規劃期程的角色,把概念發展的工作留給藝術家。黃雯說,畢竟自己不是創作者的角色,若有緣能夠一起從頭發想很好,但也要尊重藝術家的意願。
疫情後,黃雯也發現自己和兩位藝術家對於國際發展的態度有所分歧。即便在國際旅運尚未完全恢復、疫情仍舊起伏的2022年,武康和威嘉對於國際交流與巡迴演出仍躍躍欲試。但黃雯表示自己現在對於國際合作的心態轉為隨遇而安,雖然有一些企圖,但知道以自己的心力而言,可能沒辦法做得很完整。而她也認為,國際巡演的經驗需要被傳承,若目前談定一個國際演出專案,她會更傾向讓年輕一輩的經理人接手處理。但對藝術家而言,新的國際經理人需要重新培養默契,合作的安全感也需要被建立。
七、認可身為一名製作/經理人的「心之所向」
黃雯直言,如何在補助機制和原創的藝術概念之間找到平衡,是現階段自己和驫的藝術家間新的磨合課題,而這個課題中,也顯現了自己角色的轉變。她認為自己初入行時,比較是以藝術行政的角色,來服務藝術家的需求,但現階段在製作人與經理人的位置上,有屬於自己的觀察,也有個人的關注,自然會跟過去不太一樣。此外,她也認為接下來應該要試著找尋、培養其他可以跟武康、威嘉工作的年輕經理人,除了讓經驗可以傳承,也是為了讓舞團能有更永續的發展。
回到作為藝術行政管理人的身分,黃雯坦言自己對於未來向來沒有太多規劃。自己每年可能都會有一些目標,但她認為超過四、五年以上的計畫,基本上都會變成幻想,也不太在意自己在藝文環境的定位,比較順其自然。
「像藤蔓走在藝術創作的森林中,每個創作者都像是一棵樹,而我攀爬環繞在樹林之間,透過不同纏繞方式,感受到不同的溫度濕度,也看見在不同間隙與天空之間的風景。」

2019年於巴黎龐畢度中心巡演
這也許跟黃雯如何詮釋自己進入表演藝術的契機有關,用她的話來說便是「瞎打誤撞」。她認為這般「瞎打誤撞」,為她帶來了一種生命上的啟示,似乎讓她更加隨遇而安。但這種隨遇而安中,也有屬於她自己的堅持。在現今資本經濟體制主導的世界下,黃雯自許要追求的是:以藝術行政、製作與經理人的身分參與藝術生產,如何在不同的途徑中,持續維繫自我探問與靠近心之所向。無論是否時時刻刻有意為之,她認為這是在自己的實踐中,總不斷隱隱靠近的方向。

[1] 同時期國藝會成立的其他平台計畫還包括:表演藝術國際交流平台、視覺藝術國際策展平台、華文小說國際互聯平台、表演藝術華文地區推廣平台、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台、原住民表演藝術推廣平台,共七個平台。2018年所有平台合併,轉為「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黃雯後續亦擔任專案經理至2021年。
[2] 該時期行政團隊發展歷程,請參考本計畫第三篇葉名樺的訪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