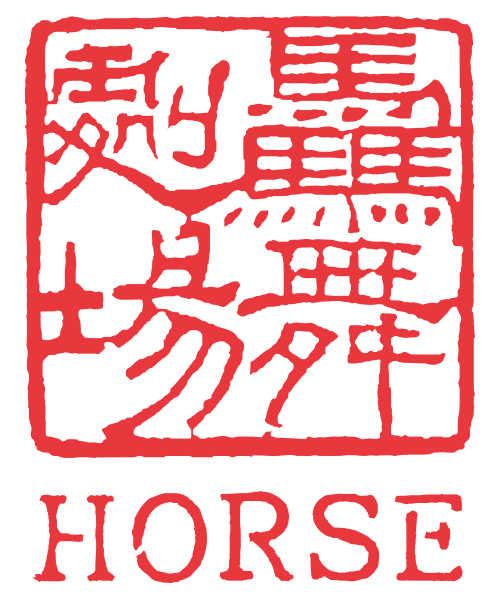即興起舞,凝視生活的哲學—藝術真心話 余彥芳訪談|2020 我的看舞筆記
文|孫玉軒

身為同一世代的女性創作人,經過時間的熬煮,已然熟成,對彼此有相當程度的信任,余彥芳、林祐如兩人都在最好的狀態裡,站在欣賞與理解的信任之上,迎來合作的機會,「我們兩個都希望前提是:我們在沒有溝通的狀態下就已經知道,我們希望給這些孩子最大的空間,支持她們去做她們自己。」一如節目名稱《換我編舞》,給予女孩們充分的自由去表達自己,兩人唯一做的事情就只是全然的支持。
這個青年世代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帶著純真的動機,讓群體裡面擁有討論的空間,能夠平等對話,形成有機的循環,將善意擴散成世代的文化。這份善意也感染了《換我編舞》的女孩們,小女孩帶著安排驚喜派對的心情進入創作,一邊思考問題更深的層次,一邊互相照顧。多年的教學經驗,讓她們能夠慢下腳步,耐心地等待,等待女孩們打開、探索,而後自主。「也有可能是我跟祐如已經決定了那個空間的文化。」從動機開始,在每個事件之間相連的通道裡產生意義,這樣的連結早在起心動念時已決定了事情最終的面貌,同樣身為創作者,在理解與加乘的陪伴下,鋪開了一種了然。
除了《換我編舞》,余彥芳這次在跳島舞蹈節《身體我的名片》帶來另外一個舊作。一個作品或是想法產出之後,有多少可以被回看的時間或空間?作品,或者是生活或者是自然,都不是一次性的觀看或經歷了之後,就可以刪除的方式來出現。這個作品裡的世界,在不同的時空狀態所進行的觀看,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撞?甚至有意識的提醒了再一次在場的人:你有什麼不同?尤其是疫情按下暫停鍵的這一年,改變了什麼?出於這樣的好奇,對觀眾、對自己,對稍縱即逝的表演藝術進行了提問。
也許作品本身沒有給予任何答案,作品的任務只是激起生物趨光的本能,觸發觀者引申、折射,打開想像,不需要多餘的解釋。「我在做的這些事情能不能勾起你的一些想法?」余彥芳用指尖點了一下桌上的水杯,杯子裡的水受到外力介入濺起了水花,水面漾起了漣漪。如果作品是一杯水,透過舞蹈這個媒介,以一種不具形體的意義穿越了身體,看見、感受、思考,作品與觀眾之間產生了曖昧的距離,當觀眾遊走在這個曖昧的距離之中,處於輕微的出神。
創作緊貼生活,生活就是在尋找創作動機。生活中經歷的大事小事,都會帶來強烈的創作動機,形式只是因著想要說的話,有意識的構築成別人可以讀懂的曲徑。看不懂的恐懼大概是讓觀眾對舞蹈卻步最常見的原因。創作者的誠意會經由作品感染觀眾,在不同的折射中思考,而非空有漂亮的形式。創作者透過作品提出問題,也許可以有意識地預見觀眾會有哪些想法,但不強迫觀眾要和創作者得到一樣的答案。「也許我的潛意識已經知道這個交會可能會發生的結果是什麼,但是我只是不從尾端去看它,我只是不從已經可見的、已知的未來,回頭去決定我現在要做什麼!」
直覺最後會成為設定,設定也可能成為直覺。
創作、生活,和即興,三者緊貼彼此,在余彥芳的世界裡互相牽動。即興舞蹈擁有一種沒有解答的特質,它是無止境的遊戲,靠近生活,也非常靠近哲學。即興如同月亮一般,始終存在著,談話、行走、飲食都是存在於日常各種的即興。因為自身狀態投射出的陰晴圓缺,外顯的光明與內隱的暗影同時存在,從月相回來觀照自己的變化,即興是和你身體的思考模式斡旋【1】,一起存在,一起生長,這個遊戲是關於對應自己的誠實豆沙包。

即興舞蹈並沒有好壞優劣的比較,可能有經驗值多寡的差異,經驗值也無關乎即興厲害與否,不過多幾個選項而已,重要的是打開了意念,讓身體在流動的過程,感受到幸福的狀態。透過沒有解答的遊戲,找回當代社會淘洗掉的身體象度,開發身體對於身邊已然存在事情的敏感度。如何面對即興舞蹈裡未知的恐懼,「藝術要發生,我們得消失。」余彥芳引用了 Free Play【2】裡的名言,身為老師在空間裡所要做也只是在人意識到恐懼、懷疑之前,解鎖踩剎車的心情。先讓身體感受當下,讓感官去經歷現場,當腦袋突然想起來要害怕、要退縮的時候,身體早已經在支持的網絡裡流動了,當身體在被支持的能量裡,自然就會在空間裡流動。「人本來就會即興!」
談起教學,余彥芳說「專業的教學是讓你的專業變成一個結構,在那個結構裡面我們都可以有安全距離的各自成長,這個叫做好的教學。」對於課堂,同樣以舉行派對的想法出發,「我比較類似是個主人,我要確保更多的人來到我的 party,他可以有各自去成長跟各自舒服的空間。」無論是熱情參與或只想獨自待著,都可以選擇自己舒服的狀態參與這個派對。課堂上所進行的練習,必須要適合今天來訪的賓客們,並且讓這些活動保有調整的彈性,這個彈性像是要呈現壽司還是飯捲的選擇。「讓很想要參與的人去社交,讓覺得有點疏離的人可以保留他自己,所以他可以有安全的位置,慢慢的去成長。」每一堂課都像是一場即興的作品,有著無法複製的精彩。
當體制內的孩子自我要求低落,將學習的責任丟在老師身上時,「我要讓我的學生做為主動的學習者,他必須要有意識他在被動的狀態。」遇到學生在體制的保護之下,帶著散漫的態度進入課堂,被動的等待老師的指令。此時需要對抗體制、對抗社會價值觀的時候,「我如果沒有自覺到不讓學生有機會去意識到他的被動會影響到自己的學習的這個經歷,我愧為一個業師。」余彥芳業師的角色散發著強烈的使命感,即使面對扭曲的巨獸,依然毫無畏懼的出擊。
往日各據山頭各自修練的大旗逐漸斑駁,以跳島舞蹈節為廊道,浸染在善意的世代,期待未來台灣的藝術產業走向如河流般綿密交錯的流動著,滋養著社會,在生活裡無止境的思考,在創作中提問,擁有身體,讓真心匯流成循環,對話。
【1】強納森.布洛斯(Jonathan Burrows),2020,《編舞筆記》,白斐嵐譯,台北:書林出版社。
【2】Nachmanovitch, Stephen,Free Play: Improvisation in Life and Art,Tarcherperigee,1991.05.01
關於作者
孫玉軒
反應弧比雷龍還要長的生物,方向感老是失靈,試圖在人類的世界跟上節奏,走著走著,就跳起了舞。害怕社交,常常因為感官超載導致過度焦慮,選擇用舞蹈說話,無論理解或誤解都是解,怎麼解都是一種觀看的態度。舞蹈是光,書寫是洞穴,剪貼迷路的風景,讓移動的痕跡開展成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