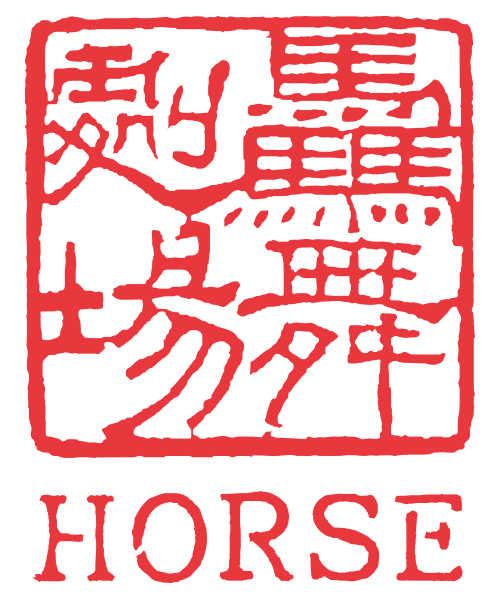張曉雄X鄒之牧|回顧摘要《重製場》第二季第二場(下)

轉身下台的《時光旅社》
鄒之牧:我也接著談一下《時光旅社》,我以前寫過一篇評論,那時我下的標題是:「五十歲的價值」。那時候我的意思是:對於年紀大的人,其實他們有一種價值在。當時的我當然不到五十歲,現在卻已五十好幾了,覺得自己那時真不知天高地厚!可是我覺得另外一方面,這也反應了他們的價值。因爲《時光旅社》是越界四位創團舞者最後一次同台演出的作品,後來也比較沒有一個正式的演出了。
張曉雄:做到2009年的時候,因為我們2008年的成績不錯,所以2009年我們的補助回來了,加了一倍,本來九十萬,變成一百八十萬,在比較充裕的情況下,我們就在想說,明年是我們越界的15週年,那我們要不要做一個紀念演出?當時本來跟一個劇場導演合作,他本來要幫我們越界舞團做舞蹈劇場的東西,結果他臨時退縮了,後來我們就找到了黎煥雄,那黎煥雄就說,好,我們來做吧!我就把我的文本遞給他,就本來《紀實與虛構》的台灣版,可是我把這個文本丟出去後,黎煥雄自己寫了個文本,我覺得那文本寫得太棒了,就把我的東西大量地抽掉,然後就按照他的做。
既然跟一個導演合作,那我們就跟著他的步伐走,我跟曉玫就負責編舞的部份。其實當年在想的是,我們老人家就藉這個機會告別越界,把越界交給年輕一代。那時候楊孝萱剛從澳洲回來,她兩次得到全澳最佳女舞者的稱號,是個非常棒的舞者,然後我們有一群年輕的,比方說舒涵、黃翊、建緯,他們的身體每個人都不一樣,我們說未來不如交給這些年輕人去發展,讓孝萱去帶領。結果我們就做了這一檔作品,等於是世代交替的起心動念。
鄒之牧:我後來發現,黎煥雄那時候是講說這個文本是駱以軍的《妻夢狗》。完全看不出來!因為黎煥雄在做這個的前一年,他自己做了一個《妻夢狗》,那個可能是更忠於駱以軍的,可是那個完全跟你們這個是不一樣的。
張曉雄:我在裡頭演那個老船長嘛,我死去後,靈魂被困在這個旅社裡頭。裡頭有我寫的一段詩,也有用在香港和澳洲,大概是這樣,「雨,夾帶著落葉,摔打在窗上,天花板滲下來的滴答聲,在遠近清晰而又模糊起來。窗上的雨,是你淌下的淚還是昨日的淚水,化成了今夜不歇的雨。不歇的雨,若能洗去心頭的屈辱、哀痛,與無盡思念,那孓留的一切,又會是可以重頭再次譜寫的空白一片?」,大概是這樣。
鄒之牧:我覺得這個作品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的一個ending。這個作品是在北藝大舞蹈廳的舞台上,可是它整個場景的搭建,你會覺得好像在中山堂光復廳,很有歷史的感覺。這些第一代的舞者就穿梭在中間,有種很虛幻、不知所以、不知道他們在演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的關係是什麼….。他們的互動是很清楚的,可是你不清楚情節跟故事、可是好像不重要,因為整個東西跟時光的流逝有關,這跟他們一路走到十五週年,好像也是蠻適合的。
張曉雄:我們十五週年的演出,其實票全部賣光光,非常受歡迎,可是六天之後,大家就決定要把越界關掉了。因為曼菲的離去,其實給大家留下很大的傷痛,跟一些負面的能量,在那個時間點上結束不是壞事。因為緊接在宣布結束的一個禮拜後,我母親過世了,我在處理母親後事的時候,自己也陷入非常大的低潮。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卻得到一個很棒的邀請,就是我們經過兩三年的努力,簡珮如在紐約幫我們牽成線,所以越界舞團將第二次回到雅各之枕藝術節。那是非常大的榮耀,可是我必須在這些打擊之下,再振作起來。那時候應該說張媽媽在天之靈有幫一把吧,因為我們要去的時候,我們得到的唯一經費來源,是來自於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非常感謝他們雪裡送炭,就給了我們機票,接下來就拿不到任何經費。然後我在想要不要去,怎麼去?我要帶三個舞者去,加上我四個人,總得生活吧,後來其實多了一個舞者,四個舞者加我五個人。
這時候突然學校發了個通知說,張老師,我們按照學校老師的福利,會有筆四十萬的喪葬費,就在我處理母親後事的三個月之後。我說我們去紐約的機會有了,然後我們就去了紐約。我們在紐澤西大學駐村,跟學生、跟舞團合作,然後在那首演《蝶夢》,《蝶夢》演完了就去雅各之枕,之後就回到紐約,在紐約市中心的舞蹈中心演了兩個作品,一個是《蝶夢》,另一個就是《時光旅社》,我編舞的那個片段,我簡稱《旅社》;同一時間,紐約的國際學院舞蹈節也在開幕,越界派了另外一個隊伍,演了《鏽蝕之牆》,所以同時三個作品在紐約登台,就有了很漂亮的結束。我覺得對我來講,我對越界舞團有交代了,然後我們有很多年輕人也冒出來了,我覺得也是一個將責任跟重擔卸下的一個機會。
當然我還是沒有停止我的創作,後來我有一陣子,在我還沒接系主任之前吧,我就不停地帶著舞者,參加國際的演出。那些都是我在國際上的一些connection,從外面帶資源進人,舞者帶出去,大概做到2015年吧,然後才告一段落。我想就是曼菲的精神怎麼樣傳承下去,怎樣把這些年輕舞者,推到國際舞台,我想多少有點使命感。

曼菲的遺產
鄒之牧: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下,這次曉雄找我來談越界,對我來說也是一件蠻特別的事情,因為我姐姐是認識曼菲的。後來我姐姐也得了跟曼菲一樣的病。所以我對於曼菲很多的資料,以前其實都是沒有辦法去碰的…。這次因為這個對談,才整理了一些…,anyway對我來說,這也是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跟時光、過往都有關係。
張曉雄:我拍曼菲的紀錄片時,有一天導演問我說,別人在談曼菲時,都不會不說曼菲非常閃亮、非常疼愛他的學生。我說那有點可惜,因為對我來講,我看曼菲大概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就是她讓舞者成為明星。第二,作為一個教育者,她的愛是非常飽滿,而且是非常慷慨的,她一直在給這些年輕人創作機會。那作為一個編舞來說,她在那個時代是用另外一種面貌出現,因為那時候,台灣陷入一種東方美學的概念,每個人都在那裡想盡辦法多少道彎,從中去找東方的辨識度,但是那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後殖民文化的影響,它就是西方人想看東方的身體,然後我們拼命投其所好,去扭曲自己的身體。大家明明穿著洋裝、牛仔褲,我們還想辦法去扭三道彎,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我當時也不太能接受。但曼菲她就很率直地告訴台灣,台北人是怎麼生活,怎麼行動,怎麼思考,怎麼戀愛,怎麼心破碎,她很坦蕩,不需要去做那些裝神弄鬼的東西,也不需要去像上一代的人,那麼苦大仇深、國仇家恨,歷史的包袱,都要扛在身上,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分水嶺。
另外一部份,她對學生很慷慨的情況下,她很多在學院的創作,不是挑好的舞者來跳,她是讓剩下的人都要給他們機會上台,所以她編了很多大編制的作品,然後就拼命把舞者打磨,送上舞台。這就是我們在講教育的那種大度,或者就是機會平等這件事情,我其實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曼菲有時候也跟我說,那個新的編舞家他很害怕,老師們都把好舞者搶走了,先讓他audition好不好,我說好,那就先讓他audition,剩下的都歸我,大概就是這樣。所以我的舞者,大概都是四十位起跳的,四十位到六十位,很多,大家都不要的我都要。因為排人少少的舞者,比較好排,比較容易體現編舞家對作品的精神跟藝術追求,但你排四十個人的時候,你已經管不到這個了,教育是放在第一位。對我來講,這是曼菲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在排完這二十五年,大概一百多個作品,六十幾個給北藝大,只要是給七年一貫制的,都在三十位起跳。所以我想這就是我們怎麼樣堅持去把曼菲的教育精神,跟慷慨,還有他對教育的看法,對藝術的看法,把它傳遞下去,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財產。

觀眾Q&A
陳武康:接下來是現場觀眾提問。
觀眾:曉雄老師,我想請教您在離開中國之前,學習舞蹈的過程,因為我看您的《野熊荒地》有寫到,您在念暨南大學,或者說到鄉下蹲點的時候,就已經能夠去教舞?
張曉雄:那叫膽大妄為,無知者無畏。我十一歲離開家,十三歲被送到中國,正好是文革剛剛結束,大概它最狂熱的那個階段,因為我們在路上的時候,林彪摔死了,9月13日。中國進入文革的第二個階段,一個相對平復期。所以在1972年的時候,叫做復課鬧革命,以前是停課鬧革命,停了六年,所有學校全部關閉。1972年全中國的學校恢復上課,然後就進到教室裡頭,當時很大的衝擊是,時間一到七點鐘,全國高音喇叭廣播,每間教室同時響,一首首唱過來,然後你發現所有的同學都會唱,從苦大仇深的《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到什麼《杜鵑山》、《海港》、《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每個人都會,就覺得毛骨悚然,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那時候全國要恢復秩序,所有的政府機構、教育單位,都要派聯合隊,一個叫工人宣傳隊,一個叫解放軍宣傳隊,軍代表和工宣代表踏進來的時候,就要穩住每個單位的派系,就這樣平息爭鬥,恢復社會秩序。第一堂課軍代表進來,就寫了個字,馬,然後問你們認識這個字嗎?底下的小朋友就說馬。OK,馬是什麼意思,可以想得出去嗎?我就舉手,「走馬看花」,成語就來了,因為小時候都學過嘛,然後所有馬的東西,我就給他五六個成語,結果老師在旁邊偷笑,軍代表也放不下來了。他其實要把你引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也就認識那幾個字。我就東扯西扯,扯到各種成語。他說這個小孩好出風頭,我就沒有,我就是積極好學而已啦,就是告訴你說,雖然打仗時,我荒廢了兩年學業,可是我還是有繼續自己讀書了啦,十三歲的人,一直想告訴他們這個。結果就打了叉叉,說這個小華僑愛慕虛榮、愛出風頭。但是我的語文老師他很疼我,因為這樣很疼我,他說你這個小華僑以後少說兩句。好,以後一定謹言慎行。可是你想你十三歲到十八歲這段時間,你有很多想表達的,但是那環境不能表達,怎麼辦?就找出口。1974年我們下鄉勞動,有人說,小華僑聽說你會唱歌,我說這不是大家都會嗎?可是你會唱我們不會的歌,那你會搞文藝,來教跳舞。啊?會唱歌,教跳舞,這事情連不起來,但是好,為什麼呢?因為只要我晚上去教跳舞,我白天不需要下地勞動,我就帶一群十六、七歲到十八、九歲的農村大哥哥、大姐姐們,在打穀場上教他們跳舞。平時人家在跳革命的各種舞都看,看了就模擬幾個動作教他們,壓腿這些東西也可以教嘛。我經常會跑到音樂教室,趴在窗口看人家怎麼練功,就照搬就教他們。十五歲的少年,根本沒什麼恐懼的,有個機會做你就做了,所以我還沒學跳舞,我就在教跳舞,想想真是膽大妄為。
等到我們學農結束了,整個隊伍全部拉回去了,公社就把我留下來。他說聽說你們那個小華僑很會跳舞,我們接下來冬季的農閒,就是晚稻收完了、農民沒事做,怕那些年輕人搞三搞四談戀愛的,就全部集中起來,政治學習,學文藝,所以我又去教他們跳舞,還教他們樣板戲。那個時候其實是你被逼上去,但是你不想示弱,抓住這個機會你就做了。結果回到學校的時候,音樂老師說,小華橋我們要組織舞蹈隊的男子隊,你來當隊長,我說好,然後就給了我那一隊的小學弟,天天給他們拉筋、壓腿。所以從小就是學著怎麼樣從老師那裡,或者聽課的時候去得到這些訊息,轉換成自己執行,然後教給我的學弟們,因為我要對他們負責。我教學的能力,大概是那個時候誘導出來。
我1972年搬到杭州,我在杭州大學後面的一個學校,原本的杭大附中,那時候已經是全國重點中學,現在也是全國重點中學,它每年考上大學的都是榜上第一名的。1976年,我們在音樂教室,冬天很冷,沒有暖氣,零下九度,我們沒有把桿,都是摸著那個窗台,做把桿的練習,你摸完這邊,回過頭來,手已經僵成這個樣子,繼續跳。後來我1977年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學校的工廠工人,幾個禮拜之後,我的語文老師又救了我一次,直接跑到工廠說,張曉雄你出來,你要不要當老師?我說我要,不管是什麼,趕緊救我吧,我每天在這都覺得我快死掉了,非常痛苦。所以我第二天就去教課。第一篇國文叫《鐵人王進喜》,講的是大慶油田工人模範。結果在1995年的時候,我被請到東北去教課,就在大慶油田,就教了一批孩子,那孩子當中,有個後來成為國際舞蹈名師,如果你們有看湖南衛視的《舞蹈風暴》,那個舞蹈總監就是當中一個小朋友。
大學的時候,繼續玩舞蹈,我是一個徹底不務正業的學生,最沒有專業思想。這是被寫到我的罪名裡頭的,「此生無專業思想」,那是一個很大的罪,在中國,就說你沒有為革命而堅持。我們的年代就要做成一群人都在談自己的理想,大部份大陸的人就是說,黨給了我機會,我一定要珍惜這機會,然後在專業上怎麼樣又紅又專。我就直接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被選進歷史系,因為我最大理想是成為文學家,我要寫作,但是我說既來之則安之,我會把歷史學好,因為歷史是個很重要的基礎學科,它會對我未來寫作有幫助,我一定會把歷史學完。但因為這樣一句話,讓我四年背了一條「此生無專業思想」。所以我的論文,縱使專家給我優秀,我是全班三十幾個人,六位優秀之一,我還是被拉下來,他也不告訴你為什麼。後來我覺得,給我什麼成績都不重要,但是我對我的教授非常抱歉,我親自去找我的教授,跟他謝罪說,老師,真的是讓您受牽累了啦!

我大學畢業後就去了北京,在中國歌劇舞劇院學了半年,他們正好要恢復一套劍術。因為那時候中國歌劇舞劇院跟北京舞蹈學院,是兩個不同的流派。舞蹈學院整套中國古典舞訓練的結構,是從蘇聯專家那裡搬過來的。蘇聯專家幫助中國,根據俄羅斯流派芭蕾訓練的方式,將所有的戲曲身段,都放在芭蕾的把桿上,比方說芭蕾的手有一位、二位、三位,他就換成戲曲的手勢,就是把整個東西中國化了,但邏輯還是芭蕾把桿的邏輯。可是中國歌劇舞劇院不走這一套,他們是從中國的傳統戲曲中去找到傳統的身段,或者是武功的基礎。結果這兩個流派就成為中國的兩個對立,但又影響很大的流派,北京舞蹈學院就說中國歌劇舞劇院是土的掉渣,中國歌劇舞劇院又回說你們是土芭蕾。
從50年代爭到70年代,到80年代,突然大家和解了,各自在舞蹈中去找舞蹈的「韻」。所以北京舞蹈學院就開始做身韻,從古典舞中去找古典身體的「韻」。中國歌劇舞劇院是繼續從武術、京劇裡頭去找身段,他們找了一個民間的武術家,從一個快失傳的劍術「白鶴劍」裡,去找身體的各種韻律。我當時跟他們學這套劍,對我影響很大的是,我後來忘掉這套劍的套路了,但是你在運劍的過程當中,身體的閃啊、避啊、繞啊、纏啊,引啊,這些都是很東方身韻的東西,其實就是脊椎動力的運用。所以後來我在教學的時候,我重新回到武術,去找武術的脊椎動力運用,發現它真的是跟西方的身體實驗方式很不一樣。所以在教學上,如何把這個身體的動力,讓它產生更多的可能。
你如果可以很理性的思考,去處理這些東西,你就可以把東方的身體系統,跟西方身體系統,不是拼接起來,而是化在一起,因為到底都是人的身體。它其實不是一個符號的問題,是一個身體內在動力的問題,所以對於表演者來講,其實會有更大的空間。
台北給了我一個很棒的園地,讓我將我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原理性身體系統,去風格化,可以在這裡讓它慢慢地完成,然後去給予這些舞者。因為我們希望這些舞者走出校門,不是為一個舞團服務,因為一個舞團對於舞者的要求總是有限的,你也不知道每個編舞家會用什麼樣的舞者、用什麼樣的身體。但是當身體的觀念和能力被開發的時候,他可以無所不能,就像簡珮如這樣,這是早年我的一個理想。
當年剛到澳洲時,我開始在中華會館授課,阿德萊得大學舞蹈系與表藝中心兩所學校的主任來看課,同時給我發出邀請,在兩所學校教中國舞。他們也希望我去當學生,學習現代舞。後來我進了表演藝術學院去讀舞蹈,這是沒有文憑的學校,我之所以選它,是因為它有非常紮實兩年的課程,念完我就要繼續當舞者。那時候我二十六歲進到學校的時候,我給自己算了一下,我二十七、八歲踏出校門,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在舞台上。所以我大概就推算得出來,後來果然是在我的計算之內。
也是到後來突然發現,他們之所以看重我的教學,是因為他們在我身上看到瑪莎・葛蘭姆的影子,可是那時候我對瑪莎・葛蘭姆是誰,我一點印象都沒有。後來學校主任在講舞蹈史的時候才講說,瑪莎葛蘭姆是從鐵雄・聖・丹尼斯過來的。鐵雄・聖・丹尼斯,他迷戀東方的舞蹈之外,也迷戀東方的戲劇,所以他跟梅蘭芳是好朋友,他把很多戲劇身段,融到他們的訓練體系裡面來,所以瑪莎葛蘭姆是間接地拿過東方的元素。
那時候就讓我思考說,既然你可以從我們東方裡頭去拿東西,建立你的系統,那我們東方人能不能夠建立我們自己的東方當代系統?其實我那時候一直在寫問號,所以對老師來講,這是問題學生,經常一臉凝重地眉頭皺成一團,老師說,走走走你離開我這邊,我需要一點正面能量。

觀眾:老師我想要問,就是現在這個年代,大家很講求「自己的」身體,可是離開了學校訓練之後,就沒有特別學所謂的技巧了。我一直擔心,還有想要問說,你的「曉雄技巧」,你打算怎麼處理它?因為非常重要,我自己本身是使用者,我一直都很驕傲,我生長在你跟曼菲老師的年代,那個東西不只自己受用,也看到很多人去轉化。我自己的疑問是,大家現在都在講「自己」的時候,你們這些技巧跟技術課,還是無可替代,那像你現在已經這個年紀了,這個東西,你打算對它怎麼辦?
張曉雄:我後來一直抗拒要把我的課整理出來。第一個,我不想讓它成為慣性的套路,我知道台灣跟大部份亞洲國家都一樣,對於升學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所以一定要像背書一樣把所有東西背熟。但是我的東西,我希望它不是在講一種風格,它也許是一種風格,但是它不是我的重點。我的重點是身體能力的開發,觀念的開發,當你建立一種觀念跟能力的基礎,再來就是怎麼樣活化使用它。我從一來台灣,就希望提供給所有的舞者,當你們有這些訓練的時候,你其實需要一個東西是,將這些點狀的東西打破,然後建構你自己對身體的認識,所以你才會是一個積極的身體主導者,而不只是單一的從導演那裡得到學習,你要怎麼編舞、要怎麼給,要向東向東,向西向西。那是一個很被動的,反射性的回應。所以我一直覺得,一個好的表演者,一個好的舞者,他是可以將訊息主動轉換,而且可以提供給編舞者更多想像的。
至於我這個系統,它未來會不會被保留下來,我管不到這些。但是我可以繼續把這些觀念,繼續告訴走進我教室的學生。我去年上半學期排《浮生》的時候,我幾個排練助理都非常depress,說老師,學生快不起來,做不到sharp。我說,「快」跟「sharp」,這是要有很大的身體的共進能力,那他沒有這能力,你生氣也沒用。那回過頭來,還是回到基礎,foundation,就是說告訴他們,你們上芭蕾課要注意什麼,你們上瑪莎要注意什麼,你要上某某老師的要注意什麼。然後回到我的課,你要把這一些東西,怎麼樣整合起來使用。我每天都會給暖身課,結果到了下半年,這支舞跳出來,就跟上半學期完全不一樣了,學生就非常鋒利,速度感已經超過上一屆。
這些東西要被建立,是急不來的,但很可惜的是,走出校門還有機會繼續這麼過嗎?這就是我們應該面對的台灣大環境的問題。可是當你想要的時候,你會用不同方法對待身體。也許是,我缺乏這些東西,我做不到速度的時候,那我的選擇是什麼?就像我們當時說,老舞者上台,要讓他們慢慢走出那一生的漫長,走出那個質感來,why not,你懂意思嗎?像野生動物那樣生猛的時候,曾經有過,你可以繼續走,很好,沒有的話,就轉向,你不一定要像小鹿那樣,可以是大象,也可以是河馬。我覺得走出校門就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啦,但是起碼我們能給學生這個foundation,他可以選擇走向國際,或者留在本土,或者是放棄,轉換其它行業,但只要這些是正向的經驗,他都可以轉化到其它領域裡頭去。
文字整理:吳孟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