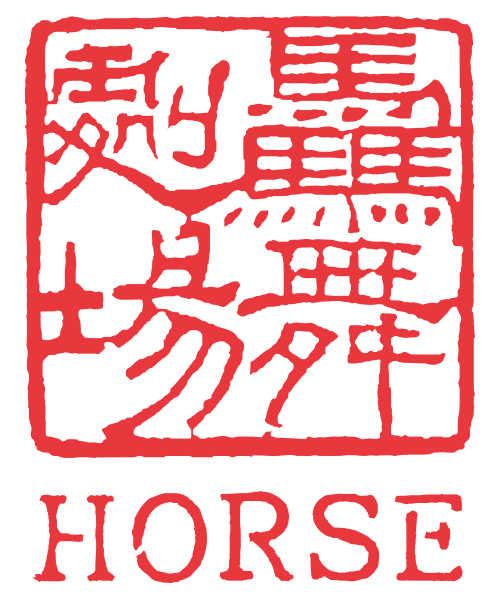張曉雄X鄒之牧|回顧摘要《重製場》第二季第二場(中)

鄒之牧:這是英國的編舞家嗎?
張曉雄:對,夏洛特.文森(Charlotte Vincent)。夏洛特其實是女性主義者,而且她本來是個女同志,結果她來台灣排了這次舞,她回去後她決定要結婚,因為她覺得結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為她在跟我們工作過程當中,她享受到一種美好。曼菲,明霏、鄭淑姬,還有雲門的第二代舞者王維銘,我是演曼菲的老情人。
鄒之牧:這個燈籠是林克華的設計?
張曉雄:對,林克華的。
鄒之牧:那時候我寫的時候,我還說我覺得燈籠弄得特別誇張,感覺是很有味道的,就像西方戶外的婚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荒謬感。
張曉雄:我們看夏洛特的作品,她非常舞蹈劇場,而且經常講暴力的,尤其是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所以我們剛開始看的時候,就想說確定要跳她的作品嗎?充滿著各種張力,非常大的那個衝擊,所以有人就決定不要跳,因為太傷膝蓋了,有很多跪、落地。然後曼菲說她要跳,我說你跳我也跳,就又在舞台上成了他的老情人。
曼菲很勇敢地把自己丟來丟去,可是我知道她每一個著地都很痛,所以我就要很小心地去關照她,就是動作完成的那個落地,但我又要假裝很無賴,因為我在這裡要演一個負心漢,就是既愛她,但又保持距離這樣,這個就是需要有情緒上的拿捏,我想這就是表演好玩的地方。你如果只是在演你的人生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一點意義都沒有,但如果你可以挑戰人生中不可能遇到的事情,這表演才會有挑戰跟滿足感。
鄒之牧:這個作品舞蹈成分很大?
張曉雄:對,其實一直跳,跳的很累的。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曼菲那個時候有很大的勇氣,她對於舞台,她很享受,這也是我跟曼菲跳的最後一支舞。好吧,我們就到這裡,話筒給你,我講得太久了。在這之後曼菲2003年就排了另外一個作品《沉香屑》,2003年底,我們就去了香港演出,那也是曼菲最後一次到香港演出,2004年這個作品就巡迴,2005年我們繼續跳,包括《蝕》。
鄒之牧:聽說是即興四週後出來的一個結果?
張曉雄:對,我等一下跟維銘有一段雙人,其實我們在首演的前兩天,我們還出了個事故,就是有個動作,我要旋360度過去,他要接住我。維銘那天說,你能不能放開一點做,我說好、維銘準備接招,維銘說沒問題,結果我就從比往常更遠的地方起跳,在空中平飛過去,然後360度旋轉,他要接住我,結果王維銘想要救我,他覺得我可能達不到,他就往前,他這一往前的時候,我還沒完成我的轉體,我的膝蓋就把他牙齒給撞裂了,他就啊一聲叫,我就從他的肩膀後面往地上扎下去,我的脖子咔嚓一聲,然後就覺得我半身麻了。我就嚇到了,我說張曉雄你不會癱瘓了吧,大家就很緊張,我說你們離我遠一點,我要自己慢慢恢復,後來冰塊敷上去了,後來站起來還好。但是後來我頸椎就有點問題了,有點傷,我很少受傷,但是我來台灣有兩次很嚴重的傷,這是其中之一。還好我沒事,我要繼續跳,我就把那360度給改了,不要再做360度。
這些雲門的舞者,在有非常豐富的舞台經驗之後,他們離開舞團,他們身上有很多能量,還沒有被發揮,這也就是當初為什麼要成立越界舞團,為什麼那時我們有個很大的共識,就說我們要繼續為這些成熟舞者提供舞台,否則的話太浪費了,就是他們到30幾、40歲,他無法承受舞團full time壓力的時候,可是他們身上還是有很多很寶貴的東西可以發展,可以把表演推向另外一個層次,這個越界可以做,所以當初我們非常積極地去promote這樣的一個平台給這些舞者。這段雙人其實非常漂亮,有些難度也蠻大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不是在跳舞,是在表演,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那王維銘我覺得他是台灣少數在九零年代中的時候,能夠創造角色的人,很多人只會跳本色,只會跳自己擅長的,王維銘是可以去創造不同的角色,而且每個角色都很鮮明,他是個很棒的表演者。明霏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歡的舞者。
鄒之牧:王維銘那時候是很有名的,後來他自己也有很多創作的發表,明霏也真的是天生條件就很好。
張曉雄:當時是九零年代末,她是原來五大花旦之一,就很漂亮。她、許芳宜、章佞、周怡,還有蔡慧貞,就她們5個人,性格質地完全不一樣,後來這些人離開舞團之後,其它人就開始冒出來,也很漂亮,下一波就出來了。
鄒之牧:夏洛特是英國文化協會引薦的嗎?
張曉雄:對。我們跟他們合作談了很多年,他們就推薦了夏洛特。她在倫敦是個很知名的一個女性編舞家,一直以女性編舞出名,回去就變了。
鄒之牧:這個音樂是她自己找的嗎?
張曉雄:對,這個是編舞家自己找音樂,因為她用了很多東歐的民謠。
資深舞者的克里斯馬(charisma)
鄒之牧:這個作品我當時就覺得看得出雲門當年第一代資深舞者們的個人魅力,我不知道等一下有沒有機會談到《時光旅社》,就是說我覺得資深中生代的人,是不是能有一個舞台,可以把他們的生命經歷跟技術呈現出來。剛剛也講到「舞蹈劇場」,其實舞蹈劇場也很適合這一代的舞者;像北藝大的吳易珊老師,也弄了一個「易製作」;吳易珊的第二個作品也有請曉雄老師去作最後的「彩蛋」演出。
張曉雄:其實作為一個表演者來講,他應該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但是作為一個舞者來講,他必須面對體能的限制,但是當舞蹈成為表演的時候,它其實是有很多可能性可以被產生,尤其是當你的思想成熟度,你的閱歷跟你的觀察力,跟你對議題的掌握到位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大的能量可以被發揮出來。那時候越界的存在,的確是很重要的一個標誌。
鄒之牧:真的,所謂太嫩的舞者真的是沒辦法做得到的!所以越界後來開發了那麼多不同的素材、題材跟方向,我覺得也是一種鍛煉,一種呈現。
張曉雄:因為人生就是個世紀風景,嬰兒期有嬰兒期可愛的地方,青少年期或青壯年期有他最寶貴的東西,那我覺得我們經常容易會用另外一個層次去比較,就是不同年齡層的東西,我覺得會有點不太公平,就是說年輕人應該有年輕人的舞台,他們的舞台應該讓他們盡力的去揮灑,但是對於成熟的表演藝術家來講,他們也應該有他們的舞台,可以不停地去提供一些人生的經驗,或者一些感悟分享,我覺得這樣的話,它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
在這之後,其實曼菲就覺得說,越界要不要結束了?我說其實我們可以讓更年輕的舞者來加入越界,因為台灣就那麼幾個團,職業舞者就那麼多,我們每年都有那麼多優秀的畢業生,或是出國又回來了,他們沒有這個舞台,如果我們覺得累不想做,我們能不能把越界作為一個年輕的、或者中生代的這些編舞家,一個過渡的平台,那曼菲就接受這個意見。
所以2002年的年初,我就發表了第一個作品《BEVY》,就是一群遷徙中的鳥,簡易來說就是漂鳥之歌。那時候明霏有跳,還有一些剛畢業、還沒畢業的學生都有參加演出,後來他們真得就走上國際舞台了。

點一盞燈,世代交替
大概2004年的時候,我提了個proposal,因為曼菲把舞團交給何曉玫跟我,就說曉玫是團長、藝術總監,那我就share,每年就share半年的檔期,我就在04年的時候,先帶著我們的在校生參加了新加坡藝術節,大受好評之後,就達成跟新加坡的合作計畫,所以就有了《支離破碎》這個節目。有兩個新加坡舞者來參加這個演出,一共七個舞者,六個男生,一個女生,裡頭除了職業舞者之外,超過三分之一是在校生,那時黃翊跟簡珮如剛升上大二,他們就參加了這個製作。其實更早的時候,吳建緯跟黃翊都會跑來說,老師我能不能看越界的排練,我們都會跟他說,要來看排練可以,但你要服務老師們,比方說先掃掃地,然後旁邊做場記、拍照,所以其實我們也在用另外一種方式帶他們,讓他們知道團隊合作所有的這些細節,跟所有這些組成部份是什麼。
我們當時那檔演出拿到很少經費,大概二十幾萬吧,交完場租跟基本的技術人員費用,都還不夠,那更沒有舞者的pay,怎麼辦呢?我們就想說盡量省錢,我們不要工作人員,我一盞燈由舞者推,我只要一個舞監就夠了。那時我提出這個idea的時候,所有人都瘋了,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我說可是沒有錢那怎麼辦?我們服裝總要吧,服裝兩百塊一件,自己手縫,所以建緯跟我一直在縫所有人的小褲褲跟tutu,然後做了一盞燈、由舞者來推。其實當時有一個概念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有非常少的資源,那對於舞者來說,他需要什麼空間?只要有一盞燈、一個舞台,然後美麗的舞者還是一樣會美麗,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可以推的燈,這個燈在地面推的時候,它只要角度改變,就會重新切割這個空間,讓一個黑盒子的空間產生無限的可能性,可以是斜線的,可以是仰角的,可以俯角的,可以背光,直接把燈推到牆那邊,打在牆上,舞者在前面,它是一個接應的效果。
所以透過一盞燈,我就整整寫了一本筆記,這個燈要從哪裡推到哪裡,要換什麼角度,在哪個音樂點,都把它很仔細寫出來,也包括舞者的動作。我們說好,既然舞台那麼簡約,我們把舞蹈的動作也重新解構,用一個最理性、最抽象的方式來呈現,就是說舞者的動作丟掉這些既定的舞姿,直接從威廉・佛賽的系統,六點、十二點的關節空間的即興,或者是雙人的即興,但是我們不一定要寫英文字母,我們寫數字,我們寫符號,那就開始操作。後來我們再把東方最厲害的脊椎動力加進來,動作就被改變了,讓時間、空間更扭曲了。
當單一符號加上脊椎動力的時候,它可能就會產生一個三維的、四維的想像,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就寫了厚厚的一本。我們做了很多遊戲規則,就是說我們從哪一點開始,然後要走什麼樣的曲線,然後這個曲線要經過哪裡,用什麼樣的力度,都寫好,寫好之後就跟舞者工作。其實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講,它產生出台灣當時看不到的東西,它不是西方的東西,它還是我們東方人用自己的邏輯思維方式,來做一個身體的表現。
這個作品有個主題,就是假如生活的記憶被呈現出來的時候,它一定不是個完整的東西,它一定是被你的主觀選擇、篩選過,丟掉了一些,保留了一些。那為什麼有些東西被保留,有些東西被遺棄了呢,再深挖下去,就有很多心理學層面的東西。如果再往下,你會發現說其實真得被遺棄、但是又揮不去的記憶,通常沒有顏色,是無色、無味、黑白的,那麼它就符合我們的舞台,只有一盞燈、沒有顏色,舞者的服裝,也是膚色跟黑色,也可以回應這個主題。那你選擇跟遺棄這樣的記憶,記憶被遺棄了又恢復,這跟你的生命有什麼關係?我們其實還是用比較邏輯的方式來推理,於是就產生了七個片段。
當時我大一有個學生叫吳建緯,他就負責拍攝,我說你愛怎麼拍就怎麼拍,只要不要影響我們就好。結果過了十五年之後,我今年開始整理我的錄影,幾百盒帶子,請學生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整理,然後突然看到這個影片,我傻眼,就說這是誰拍的,一直在找那個攝影師是誰。因為他對著鏡子拍,但是你看不到他,最後有個鏡頭穿幫了,他把自己塞在牆的夾縫裡頭,從下面往外拍,然後他沒有三角架,他用了一台破機器在錄,可是要錄出來還蠻有趣的,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一段《支離破碎》,可以看到當年我跟黃翊他們在工作的狀況。後來簡珮如因為跳完這支舞,她覺得她應該要成為一個職業舞者,我在想說,不小心中下這個種子,然後長成大樹,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鄒之牧:那時候我寫說:「新生代舞者簡珮如的精準跟美感,令人眼睛一亮」。
張曉雄:是,因為它有六個男舞者的能量,跟一個女生做對抗,她完全不怯場。其中另一個男舞者,他原來是香港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他是有史以來最矮的舞者,不到一米六。他是越南裔的荷蘭人,很小的時候到了印尼,然後被荷蘭政府收容,在荷蘭長大、進入舞蹈學校,荷蘭舞蹈劇場季利安之前的那個總監,很喜歡這個學生,曾經以他為模特兒,拍很多攝影作品。後來他進了雲門一年還是半年,他就離開了,回到香港。那我因為在80年末、90年代初的時候,有讀到香港芭蕾舞有關的訊息,我對這個人也還蠻熟的,所以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不跳舞?他說老師不要跳了,我都老了,我說別這樣,你那個無敵腳背出來就夠了。然後他就參加了這檔演出,他唯一提的要求是,老師我的腳背太大了,不能跪地,我的膝蓋太痛了,不能滾。我說好,那麼往空中發展,就給他發展了一段非常厲害的雙人,因為他的身體柔韌度跟力量的掌握非常獨特。
鄒之牧:跟李偉淳嗎?
張曉雄:對,跟李偉淳。
鄒之牧:老師剛講那位是黃建彪,非常個兒小,可是他真美。
張曉雄:一米五幾。
鄒之牧:老師那時候還出了一個節目單吧?裡面好多攝影。其實這裡面也有黃翊的攝影作品,也有老師的。
張曉雄:我當時帶了黃翊、吳建緯還有駱思維,我說你們如果未來要做創作,一定要會另外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那攝影是最容易達成的,所以說他們一進校,我就一直帶他們做攝影,這一次就放手讓他們去拍攝。海報是黃翊拍的,裡頭很多照片是建緯跟思維拍的。
鄒之牧:這個作品當初是在實驗劇場演出,那時候我不是很懂,可是我看到的時候,我很驚訝這是老師的作品!因為老師的作品一向是很powerful,場面調度很大….,可能那時候我非常驚訝,演出的部份是完全肢體、表情是中立的,不帶表情的…,跟剛剛講的舞蹈劇場完全不一樣。是完全放大肢體的部份跟情緒;有一點像人類原型、生命原型,情感原型的東西,是個在很小的、禁錮的空間裡面,能量的放大跟肢體的放大。所以對我來說是更震撼、很powerful,我當初很喜歡這個作品。
張曉雄:謝謝!其實純肢體還蠻難做,就是要用身體去建構一整個作品的時候,身體的理性控制,跟他極致的展現,這個東西是要有很有功底才做得到。正好這批學生,黃翊那一班是我教的最多,一路從先一帶到他們畢業,所以帶到大一、大二的時候,他們的身體is ready,我就真得推他們一把,給他們這個舞台,我當時在排的時候,就是帶著這批學生。然後我記得首演那天,我旁邊坐了我的頂頭上司,她就一直罵我,她說你為什麼要讓學生來參加演出?這對其他學生不公平,我說教育的事情不是用公平論,而是說當你看到學生有可能性的時候,你一定要給他們機會,然後給不同的學生不同的養分和不同的機會,這才是教育,它不是一個罐頭生產線,所以公平不公平不是用在這個地方,而是他們需要更推一把。她說:那你在學校也可以做創作啊!我說我在學校都要做大堆頭,因為學校每年的年度展,有兩百個學生左右需要這個舞台,所以你永遠要做大堆頭,讓每個學生有機會在舞台上展現,那時候做的是練習曲,對我來講它不是作品,真正的作品不需要那麼多人,真正的作品你要每一個舞者都能夠充分的展現,這才是作品。
這就是我發現很長一段時間,我陷在一個困境中,我必須要跟這些假對立的議題周旋,那我覺得有時候會分掉很多energy,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值得堅持。我那時候得到最大的支持,就是曼菲,曼菲說:你做,然後就做了,就出現這個作品。
張曉雄:先把影片直接跳到黃翊他們,有一段是看著筆記工作,再往下,這是簡珮如跟駱思維。簡珮如後來去了美國,她在三年之內,就成為瑪莎・葛蘭姆的首席。有一個傳言說,台灣舞者其實到了瑪莎・葛蘭姆,誰都可以成為首席。不要相信這句話!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你就算成為首席,隨時都會被其它人拉下來,因為競爭非常激烈,而且他們階級制很強。瑪莎・葛蘭姆其實到後期,有很多國際重要的中生代、新生代編舞家進來編舞,把瑪莎・葛蘭姆原來作品的精神,重新用現代的方式來詮釋。這些編舞家包括馬茲.艾克(Mats Ek),瑞典國家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國際巨擘,那也有納丘・杜亞托(Nacho Duato),是荷蘭舞蹈劇場的編舞家,也是西班牙國家現代舞團的藝術總監,也曾經當過基羅夫芭蕾舞團(Kirov Ballet)13的藝術總監,他們都不約而同選了簡珮如,因為她的身體可能性不只有一種,她不僅能夠詮釋瑪莎・葛蘭姆所有的經典,舞評還說她讓瑪莎・葛蘭姆復活了。除此之外,任何一個編舞家來,她都是綽綽有餘去應付,所以她成為他們的寵兒。她後來得了很多大獎,包括了貝西獎(Bessie Awards),就美國的舞蹈奧斯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獎項,在義大利的國際舞蹈大獎(編按:為義大利Capri International Dance Award 的「傑出舞者獎」),曾得到那個大獎的是瑪戈.芳婷 (Margot Fonteyn)14、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15、貝嘉(Maurice Béjart)16這一類人得到的,她是台灣第一個拿到這樣國際大獎的人,但我們台灣好像一個許芳宜就夠了,其實我們有很多許芳宜,每個許芳宜都很重要。

鄒之牧:我看我自己當初的note,簡珮如在您這個作品裡面,我寫她是有點「機械式」的,可是她到了《支離破碎2》,好像又變成像女泰山,就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她都詮釋的很好。
張曉雄:是,尤其她在詮釋季利安系統的時候,她身體的流暢性,動力的轉換跟雙人是完全沒有障礙的。當時馬茲.艾克宣布退休,要收回所有的版權,最後一次《Solo for Two》就是給她跳,而且指定只能她跳。其實那一年如果簡珮如回台灣跳的話,馬茲.艾克答應要給她這個作品,但是後來這件事沒有發生,有點可惜。
鄒之牧:這一段就是我覺得最動人的一段,這邊是黃建彪,那位是李偉淳。
張曉雄:他們這邊還在練,因為建彪他是full time老師,所以他只有禮拜六、禮拜天才能來工作,所以這一天工作他要花一點時間去重新溫習,但你可以看到他作為一個國際職業舞者,他對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講究。
這一段叫水的記憶,它有兩個故事來源:一個是有個大陸的舞者,是國際上非常重要的舞者,他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文革,小時候父親被紅衛兵打,後來還被當做現行犯抓起來,他從小就跟著媽媽,然後去學武術,等爸爸放出來的時候,兩父子其實有很大的代溝。一直到後來,他父親不喜歡他跳舞,所以從來沒看過他演出,到他父親走之前,他跑回北京去照顧他父親,他發現他原來非常悔恨,當初可以一拳把紅衛兵從舞台上打下去的父親,萎縮到現在剩一個骨架子的時候,他非常難過,他覺得這輩子沒有機會跟爸爸好好溝通。
那同樣的故事,是黃建彪的另外一個故事,他說他記得他離開家鄉很小,而且記得前面一條河水,所以這個就成為了這一段,水的記憶,也包括了邢亮幫他爸爸洗澡。有一些觀眾會讀到兩個男人的愛情,也無所謂了,他們愛怎麼解讀都可以,這個大概是作品有趣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投射。
後來李偉淳在這支舞首演之前告訴我,他說他跳這支舞,他很掙扎,很掙扎的是因為當年他在高雄畢業演出,當時他父親彌留,他必須要在趕回去看父親跟完成畢業演出之間做選擇,他選擇留下把演出做完了,所以他沒有看到父親最後一眼,所以他跳這支舞的時候,他其實有很多內在的情感,但我希望情感是透過肢體表達,而不是透過面部表情。
鄒之牧:他之前有跟我提過,說他跳這支舞的時候very different。他整個情感,讓這一段的深度是夠的;其實我有點驚訝,就是李偉淳可以把跟黃建彪這一段表現的這麼好,我覺得他心裡的那個也是有⋯⋯
張曉雄:有一個補償。
鄒之牧:是。
張曉雄:有一種釋放的支持。我覺得藝術最好、最棒的地方,就是不管是表演者、還是創作者、還是觀眾也好,它給予個人負面經驗的一個出口,可以釋放出來,我想對於創作來講,這是很寶貴的一個形式,我們就看到這吧。
鄒之牧:我覺得這個作品跟所謂的身體雕塑,是不同的兩件事。這個作品裡面說了很多內容,像是簡珮如的角色,其實比較像是一種原型的女性角色,幾位男性的角色彼此也有雙人舞,也有跟她的互動。這整支小而美的舞蹈,其實有它非常豐厚的內容,我覺得是蠻不錯的舞蹈,並不是單單只是一個姿態,或者光影上面的美而已。那老師也可以再講講,後來有再發展了《支離破碎2》跟《支離破碎3》。其實老師我有點好奇,因為你剛剛說第一次經費很少,可是第二次的服裝簡直是大玩特玩,完全跟這個反其道而行。
拒絕知天命的浮士德
張曉雄:在2007年我們做了《支離破碎2》,就是直接跳回到另外一個形式去,因為我覺得支離破碎這個主題,可以有很多發展,只要講到關於生命的、關於來路的,那個過往的支離破碎的東西,都可以把它帶入。
在2006年送走曼菲的時候,大家都陷入非常大的低潮,我自己也是面對了非常大的考驗。在照顧曼菲的最後階段,我發現腳底越來越不舒服,有個東西在不停地瘋狂長大,那時候我把曼菲安頓好之後,我就直接到醫院去,檢查出有一個惡性腫瘤在我的右腳腳弓,那就做了一個移除、植皮的手術,所以有一個大概茶杯口的,超過六公分深、十二公分直徑的傷口。當時因為做了移植手術,腳其實不能夠著地,大概有四個多月,我是拄著拐杖的,非常痛,尤其植皮,在第一個禮拜的時候,還要重新把它撕開來再壓下去,不能打麻藥,那是我有生以來最痛的一次感受。所以我也在想說,如果像醫生講,如果它蔓延到我的淋巴系統、需要截肢,我會怎麼樣?結果後來等到做完手術,幾個月之後,醫生說恭喜你,我們清的蠻乾淨的,所以不需要做化療,暫時不需要擔心,但是在十年內要定期去檢查。
這個對我來講當初打擊蠻大,但大概我十一歲就遇到戰亂,我在柬埔寨出生的,然後十三歲之前被送到中國,我一個人在那生活十二年,所以怎麼樣照顧好自己、怎麼樣好好站在自己的腳上活下去,這件事情是我這一輩子的功課。那時候我在想說,如果不能夠跳舞怎麼辦?所以我在進場做手術之前,我就請人幫我買電腦、教我打字,我就用一個手指頭慢慢戳,大家幫我設定好了,比方說word檔怎麼用,photo shop太難了,iPhone還可以,等這幾個東西我學會之後,從醫院出來不能動,我就坐在那邊架起這個腳,然後就開始在戳字,整理我的文字稿,那整理到大學的文學筆記時,浮士德的劇本就跑出來了,那時候我的感悟突然改變了。
以前讀浮士德的時候,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出賣自己的靈魂跟魔鬼做交易,這是不可以的,但當我自己行動不便,再重讀浮士德,那個感受完全不一樣。就突然覺得,其實這是人類面對不可逆時的最後一次掙扎,是他做的最後一次努力,他不甘於人的宿命,他要挑戰他的宿命,那他能夠做的,就是有人告訴他,我可以給你這個,你要不要,我們做個交換,所以他做了一個嘗試。我從這裡讀到另外一個東西,當然我們可以說死而後生,或是什麼重如泰山、輕如鴻毛等等這些,非常理想主義的東西。但是回到現實來,當你到了這一關的時候,你難道沒有動搖過嗎?如果你動搖的話會怎麼樣?如果你動搖之後,你醒悟的話會怎麼樣?如果你不動搖的話,你會怎麼樣?所以我就提出三個問題,把它變成了舞作。
不過我不想講浮士德的文本本身,我想講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碰到了這個選擇題。像是父親用蠟做了一對翅膀,告訴你去飛,但是你不要飛太高,趕緊逃離這個地方,可是你飛起來後發現,我終於可以離開地面了!飛的感覺真好,就一直往上飛,然後翅膀熔化,就掉下來了。對西方來講,這是一個悲劇的人物,卻充滿了人的勇氣和挑戰,但對東方來講,就是你不自量力,活該你死,不聽話。所以說東方、西方,對這個有翅膀的少年,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影響。回過頭來,如果我們回到希臘的羅馬神話當中去看,這是一個原型人物,他正好點出人在宿命中,他們的選擇是什麼,不管是什麼選擇,他去挑戰、對抗,或者是逃避,都是勇氣。所以我嘗試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浮士德之咒」,就因為這樣產生作品。但是當然還是有聽到一些東西就說,這個太性感了,太情慾了,或者是太赤裸了。
在2008年的時候,扶植團隊被砍掉了經費,理由有三個:第一個說舞者技藝高超,惟有炫技之嫌。舞者表現得很好,這是不行的,我覺得這個是⋯⋯腦子轉不過彎。第二個說,浮士德之咒,沒有照浮士德的文本來演譯。對不起,本是我寫的,我不是寫浮士德,我寫的是浮士德之咒。第三個,男舞者的赤裸沒有必要。這是完全在干涉了創作自由,我不太敢相信它發生在台灣,但它發生了。
我曾經跟林老師抱怨了一下,林老師只說了兩句話,他說張曉雄,你大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你跟他們對著幹,然後你準備接各種污水往你身上潑。第二個你別管他們,繼續做你愛做的事情,做你想做的事情,堅持下去。我說好,看著第二條路比較容易,那我做第二條路,所以我們就繼續走。2008年我們做一系列的演出,出去巡迴,帶著學生,帶著舞者,出去巡迴後,我也開始說好,沒有台灣的資源,那我走上國際,我有很多國際的連結,其實我自己以前給中斷掉了,我可以把它重新接起來,拿這些國際的資源,來繼續promote我們的年輕舞者。所以我就跟香港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學生,接洽上,然後他們馬上就說,那你2008年來幫我們做作品吧,所以我們才做《支離破碎III:紀實與虛構》。
這是支離破碎二的延伸,叫支離破碎三,支離破碎三其實不支離破碎,因為你作為一個創作者,你對一個太熟悉的名字老是不停地出現,你大概不能忍受。所以我在想說,既然在講一個城市報復者的故事,那我們就叫《紀實與虛構》,如此產生的這些文本,它可以成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歷史背景,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詮釋。最後我們寫了個文本,寫了很多段詩,這些詩可以套在不同的場域,或不同的國家。香港是第一部,後來有了新加坡的《風向和去》,澳洲的《家園》,台灣的《他鄉》,和美英版的《古城》,這些都是紀實與虛構整系列同樣的文本,但完全不一樣的舞台展現。
註解
13.基羅夫芭蕾舞團(Kirov Ballet),為俄國歷史悠久且富有代表性的古典芭蕾舞團。1991年舞團因進駐的馬林斯基劇院更名,舞團便隨之改名為「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但一般仍以「基羅夫芭蕾舞團」稱之。
14.著名的英國皇家芭蕾舞團首席芭蕾女舞者,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芭蕾女舞者之一,與芭蕾巨星紐瑞耶夫堪稱芭蕾舞史上最有魅力、最受歡迎的舞台情侶。
15.著名的俄國首席芭蕾男舞者,於1961年冷戰期間,紐瑞耶夫擺脫蘇聯國安局(KGB)特務,投奔至當時被認為是「自由世界」的西歐。於1960、70年代,紐瑞耶夫與瑪戈.芳婷,不僅為芭蕾舞界的黃金拍檔,也分別坐擁世界級超級巨星的地位。
16.法國知名編舞家,為洛桑貝嘉舞團(Bejart Ballet Lausanne)藝術總監。編舞風格獨樹一格,於舞蹈史上具一定地位,代表作為《波麗露》、《春之祭》。
文字整理:吳孟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