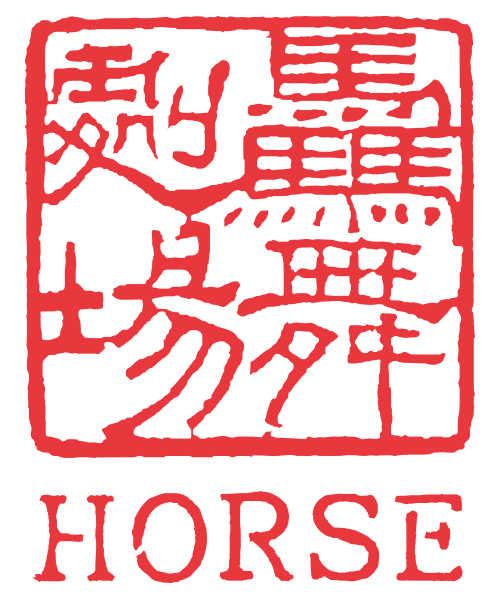古名伸 × 盧健英|回顧摘要《重製場》第一季第一場(下)

《我曾經是個編舞者》
古名伸於1992年發表《我曾經是個編舞者》,來自直覺的創作與實驗,以語言為舞譜,以音樂做結構,品嚐並鑽研關於「身」與「心」。在看似非常理性的狀態底下,身體上一秒被台詞、被語言綑綁著,下一秒將自己鬆綁,實則非常忙碌的進行身心的雙重奏。
古名伸:我的獨舞《我曾經是個編舞者》事實上是在紐約發展的,那時候所有東西都出自於一個直覺。那一支舞應該是我的實驗,因為我的舞譜就是我的語言,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在講話,所講的話都是被編寫好的,那些台詞就變成是一直不斷去唸,就整支舞裡面要把台詞全部唸出來。因為我念了台詞後,腦子就很忙,腦子很忙的時候管不到身體,那身體就可以亂來,這是我的目的。
讓身體可以亂來的這件事情,我又覺得好像還不夠,還是搞了點另外的破壞,我就到處去借衣服,借了一件好像是劍道的衣服、棒球裝、擊劍(俗稱西洋劍)的衣服,還有醫生進手術房、開刀房的衣服,還有一個軍裝,還有好像是廚師的衣服。我把這些衣服都掛在後台,讓舞台監督選擇我那天要穿什麼衣服,衣服的目地是要改變身體的行為,廚師服非常好跳,醫生服也非常好跳,可是棒球裝好難跳,有一堆的綁腿、護腿、護什麼⋯⋯那個擊劍的東西又這樣挺著,「咚」「咚」紮腰的;劍道的衣服就是方方正正的,然後手要彎都不容易,所以藉由這些衣服影響我會怎麼樣子用身體。
音樂是我的結構,裡面有四段音樂,所以有四段話,在每一段音樂要在裡面把話講完,然後結束。我跟觀眾的實驗就是有一堆東西是我想要試的,我事實上給你一個無法控制的身體,不曉得、很不習慣的身體,但是當我給你文字的時候,你們一樣照常拍手,你們全部都被表面的意義,或者《我曾經是個編舞者》這個字所收買。我在臺灣演完以後,就一直受到很多國外的邀請,我用中文就講得很好,後來到香港我就背英文、用英文版,所以它又產生了難度,後來到英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英文也已經很溜,所以我就中文加英文,唸台詞時一邊自我翻譯、中英翻譯。全部都只有一個目地,就是要把我的腦子給剝奪掉。
我發覺這20多年來,我一直想辦法要津津有味地在品嚐跟鑽研的東西——關於「身」、「心」的這兩件東西。我剛剛一出來做一個拉又一個劈腿又第二位置蹲(指《我曾經是個編舞者》影片當中的片段),是因為那個衣服好難跳硬邦邦的,我真的很不習慣那個東西,所以我事實上整個第一段都在搞清楚這件事情,然後到後來那個衣服終於比較合身,才可以亂跳。
像說我在看我自己,我都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就是卡住了」。像我第一段,我到後面的地方,那個音樂已經到了,然後我一整段的詞都沒講,反正我就聽到那個音樂cue,我就只好「blah blah blah blah」,因為我前面那個「話」被身體的行為或者什麼東西給卡住,所以我來不及、我要趕車。所以時間的拉鬆或是拉緊,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就你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剛剛有個地方,我就pose半天,是因為我那時候根本不曉得下一句是什麼,然後就pose在那邊,腦子裡面一直搜索。還有一個地方是我拼命跳也沒有幹嘛,就一直跳一直跳,我那個時候也是不知道到底下一句是什麼,因為就唸唸唸。我把那個詞都寫得像是繞口令一樣,就是有一點讓自己打轉那樣,所以很容易講一講就忘了講到第幾句了,然後頭腦在忙的時候,身體很容易就「嘩啦嘩啦嘩啦」亂跳,這時候所謂的「過去」就跑出來了,剛剛我看到什麼你知道嗎?我看到雲門!因為本人有跳過《薪傳》1的好幾個段落,所以說我會看到《薪傳》的動作跑出來,我的天啊!當然很多人都看到了我的中國舞,那個沒事就是point在那的芭蕾,就是我過去的很多背景,全部都在那個地方刻畫得很清楚。對於那個身體跟心靈如何分裂,又如何把這個分裂的地方重組,一直到現在,我第一次開博士班的課「身體實踐研究」,我就是在探討這個事情,搞了20幾年,我終於去博士班開課了。
盧健英:我雖然沒有看兩個月前古老師跳的,但剛剛武康形容是現在「更亂」,剛剛在看這支作品的時候,就會覺得其實古老師比較是在一種非常理性的狀態裡頭,整個身體還是被你的文本和台詞綁著。所以久了我們那個年紀的觀眾來看這支舞蹈的時候,還是會覺得那就是30幾歲的古名伸,她依然有一個非常理性而強大、想要去表現一些什麼東西的那種幹勁,所以對我來講會很像有一種特技的演出,一定要在幾秒內把自己綁在一個盒子裡面,然後幾秒內一定要自己脫逃,我覺得就像那些台詞、那些語言的結構把你綁起來,然後你一定要在那之前把它鬆綁。但是換句話說,現在的、兩個月前古老師跳的東西,其實已經鬆綁了,你更知道說在這當中,你跟你的身體和你的mind中怎樣做雙重。
跳舞跟生活一樣,在頭腦還沒搞清楚問題以前,身體都已經幫你解決了
觀眾提問:相比富有技巧與規則的芭蕾舞,即興強調當下的感受與選擇,是否推翻了規則(自我)的存在?
古名伸:我覺得它是最有趣的,也是這些年來讓我一直想要把它理得更清楚的,就是「我」這件事情,其實除了「自我」之外,還有一個「身體的自我」。身體事實上太聰明了,那麼多的時候都是靠身體在解決問題的,跳舞的問題跟生活的問題都一樣,你頭腦還沒搞清楚問題,身體都已經解決了。理想的狀況其實包含已經編好的東西,你每次在表演的時候,其實你也是在面對那個當下,那個當下有太多太多細節的變化,就儘管你落地的時候角度稍微不好,你接下去找什麼時候去把它轉過來,你的身體跟你的意識其實也是一直work together totally。所以說那個身心整合的這個過程,只是覺得藉由這樣的形式一直去面對、去處理、去理解、去澄清,我現在就是非常非常的肯定它必須是一個整合的狀況,不管跳任何東西,現在也覺得過日子也是一樣,是一個身心整合的過程。

對我這麼長期做接觸即興的人,其實我不會想要把接觸即興拿來做表演
接觸即興是一種技巧,它一直在談的是關於——聆聽、理解、接受、給予,造成所謂的關係,讓那個關係可以去交織一個類文本的狀況。
盧健英:我以前曾經問過古名伸說:「接觸即興它到底是一種探索、是一種訓練還是它是可以拿來表演的,它究竟應不因該成為一種表演?」但我看了古名伸這二、三十年來,這件事情在她身上其實是一種信仰、一種宗教。
我看過《亂碼》2,就是在那次裡面,我想我真正懂得古名伸要帶來的接觸即興是什麼。如果把接觸即興當作是一種生命修行的話,那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在當天產生一種新的樣態,或一種因為所在環境當下的磁場,而感受出來的一個新東西。那次看完《亂碼》之後,在那個現場我其實是非常感受到她身體的能量以及舞台上散發出的訊息,我完全能夠在那次知道什麼叫做「每一次的接觸即興是一個真實的自我的一個表現」。
古名伸:其實我現在非常非常清楚接觸即興是一種技巧。事實上接觸即興是有人在表演的,他們的表演我自己也很喜歡看,你就看到說「心性」,人的心性完全表達,你就看到說一個說:「哇!一個雙人舞,一個人很強勢很鴨霸(台語),或是有個人很調皮。」然後你就看到這種真實的人在用身體對話,我就覺得非常的好看。所以它在這種情況之下,是有可能作為一個表演的,但是對我這麼長期做(接觸即興的人),其實我不會想要把接觸即興拿來做表演,因為我是個編舞者,我覺得我是個編舞者這件事情,對我還是有很強大很強大的影響。
儘管我做即興,我在做《亂碼》時候,我只是放手把所謂編舞者的權利交付給大家,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公平、我們都是股東、我們一起來練,那我們就是當下一起用即興來練。在大家一起用即興來編創今天的演出同時,我們彼此都理解接觸即興的技巧,我們有這樣子的技巧,我們可能沒有上同一位芭蕾老師的課,但是我們都一起跳接觸即興。所以那個語彙本身,特別是接觸即興,它一直在談的是關於——聆聽、理解、接受、給予,就是這樣子的東西,造成所謂的關係,讓那個關係可以去交織一個類文本的狀況。
我覺得「即興」這兩個字,幫了我好多,但也是我的大罩門。我在這個演出完了、大師走了以後,有很多的事情突然間從天堂掉到了地獄,就大家起立拍掌完了以後,就開始想說:「古名伸,接觸即興真的不曉得在幹嘛。」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當年我們功力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時候的確不是很好看。可是我真的覺得健英剛剛說的信仰這個東西有一點大,我就覺得好像有一個選擇,那個選擇就是我覺得還有很長的路必須要去究竟,我的功課或是我跟它的因緣還沒有結束,我必須要再繼續去執行。
註解
- 《薪傳》,1978年雲門舞集於嘉義市體育館首演的長篇舞劇,是第一齣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劇場作品。
- 《亂碼》是古舞團擅長的結構即興舞蹈作品,一個舞蹈、音樂及燈光完全開放的即興演出。2018年舞團25週年製作以《亂碼2018》之名再度上演此經典舞作。
責任編輯:楊蓉、陳珮榕
核稿編輯:葉名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