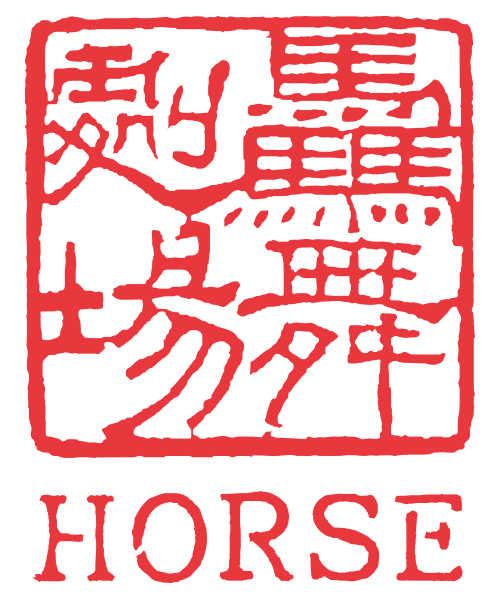林文中XDiane Baker|回顧摘要《重製場》第一季第三場(上)
「第一季的第三場邀請到兩位來賓,一位是林文中,我從小就認識他,那時候他還是一個舞者,從北藝大畢業後就一路出國。紐約村聲時報曾經報導他是個「超級舞者」,一路帶著那樣子的光環回來,後來決定開始創作,作品也備受矚目。最後為什麼在得了台新獎的隔年,決定要把舞團收起來呢?我覺得是令人非常好奇的,是給我們這個舞蹈環境什麼樣的啟示嗎?不太確定,所以很想要問問。
另外一位邀請的與談人是Diane Baker,她在台灣三十多年,是一個重度的舞蹈愛好者,我覺得她有一種客觀的立場,看著台灣這三十年來的舞蹈發展。希望他們兩個的碰撞,能在今晚為我們勾勒出過去的一些變化,以及我們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這個舞蹈風景。」 ——計畫主持人 陳武康

創團的起點之作《小》
林文中(林):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要看的兩個節目是《小》(2008),我回來台灣做的第一個作品,首演是在皇冠小劇場,隔年在文山劇場有演過。另一個要看的作品是《流變》(2016), 是在城市舞台演的。那我會先說一下作品,Diane再接著談談第一次在皇冠小劇場看到《小》的印象?
Diane Baker(Diane):我第一次認識文中,是他在比爾提.瓊斯(Bill T. Jones)1舞團當舞者的時候,我當時有訪問他。那是文中最後一次在舞團的巡演,他告訴我他準備要回台北生活,以及他即將有個來自舞蹈空間舞團的作品,叫《惡童三部曲》2 。所以我第一次看你的作品,其實是《惡童三部曲》,是一個動作很快、很俐落的大群舞,有很多的線條。我當時也有採訪他,那時文中還沒有創立舞團的打算,只是想編舞,不過當我隔年再採訪文中時,他就已經成立了自己的舞團,他因為覺得很多演出都發生在台北,觀眾想看表演,都要特地來台北,那他想要把作品帶出台北、在台灣巡演,所以就做了一個「小」的作品。他當時讓舞者在箱子裡跳舞,首演就發生在皇冠小劇場。
我曾經在皇冠小劇場看過很多舞蹈演出。如果你們有去過那裡,就知道那邊的天花板很低,那如果你看過文中跳舞,尤其是跳躍和移動,你就會很擔心他會碰到天花板。皇冠是個小型的劇場,舞台空間大概就跟這裡差不多大,文中就在那裡演一個比這個劇場還小的作品,他做了很迷你很迷你的箱子,舞者就困在裡面。我當時是坐在地板上,看著舞者在箱子裡跳舞,我覺得非常驚人!
林:早期的皇冠小劇場是在敦化南路的一個地下室,那不是一個像一般劇場有挑高的空間,所以多少有點壓迫感。我那個時候會借皇冠,也是因為我之前有幫舞蹈空間編舞,可以跟平老師借。借了之後我就想說,如何把這個環境的缺點,變成我的優點,加上那時候有一些現代舞是舞台上比較華美的,那我要不要就朝一個視覺藝術的方向去做,去用現有的資源、現有的舞者,做一個小的作品,但把人關起來,爆發力會比較強。
Diane: 我想很多人想到舞蹈的時候,應該都是會想到動作,想到擴張,也想到舞者怎麼在空間中流動,編舞家怎麼用空間去說故事。所以當空間變得很小,舞者就真的擠 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很有趣的概念。在台灣比較少人聽過,但在美國很流行養「螞蟻農場」(ant farm),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塑膠箱裡有螞蟻、沙、土,你可以看到螞蟻怎麼建造它們的巢穴。在看《小》的時候,很像就在看一個人類版的螞蟻農場,因為舞者要在一個很小的盒子裡去創造空間結構。對我來說,有趣的是看文中怎麼折磨他的舞者。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五個舞者擠在一起,舞者有時可以離開箱子到舞台上。你因為會持續想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所以不會無聊。
林:那個塑膠盒真的很熱。我後來在想要不要加一個風扇在旁邊,因為盒子是密閉的,劇場的冷氣沒有辦法進去。塑膠盒中間還有個洞,那個其實是做道具的人做錯了,但我就想說中間有一個洞也蠻有趣的。因為有一個洞,就可以從那個箱子走出來或跳出來、再進去,那支舞就有一兩個部分是舞者有離開盒子。
Diane: 我再看到《小》就是隔年在文山劇場的巡迴,那次就是在正式的劇場。在皇冠的時候,大部分的觀眾是坐在地板上的,跟舞者非常靠近,但在文山劇場,舞者是在台上,跟觀眾離得很遠。那還是一個很有趣的表演,但我某程度來說很懷念皇冠的親密感,可以很近距離看舞者、看動作,我覺得那是讓《小》的首演版很難忘的原因。
林:我創團的前三個作品,通常在台北首演後會去巡迴,隔年再在臺北演一次,那時候不怕死啊,就是覺得會有觀眾看。Diane剛說的文山劇場是長型的,觀眾就是會比較疏離一點,原本舞作的親密感就不存在了。《小》的首演版是舞者的汗真的會甩到你身上,是非常靠近的,那些摩擦、撞擊真的就是在你旁邊。
Diane: 當我回想《小》的時候,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原因是,一般當編舞家開始創立小舞團的時候,都會覺得自己要有個震撼之作,會用很多的燈光、很多的顏色、很新的科技,試圖讓所有東西都變得很大,盡可能讓自己的名字顯現。但文中完全走了相反的方向,他是用「安靜」和「小」來獲得注意力,他讓你專注在舞者和動作上,以及舞者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非常特別的。文中後來也從《小》發展出好幾個作品:《情歌》(2009)、《尛》(2010)、《小南管》(2011)⋯⋯
林:她在講「小」系列,包括《情歌》、《尛》、《小南管》和最後一個《小.結》(2013)。
Diane: 這些作品在空間上是比較大的,但都依然很專注在動作與舞者身上,也都被設計成好攜帶、好巡演的作品。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所以當武康邀請我的時候,問到哪個作品是我最想談的,我就想我們必須從《小》開始,因為某種程度來說,那是文中創團的起點。第二個我想談的作品是《流變》,因為這是文中開始往「小」的相反去了,他開始往大舞台走,做大的動作,大的表達,這代表了文中進入編舞的下個階段,在《流變》之後的三或四個製作,動作都開始變得更流暢、更流體。
年輕的直覺,親密的觸感
林:我這次在剪接《小》的時候,發現這個作品其實是蠻直覺的,所有的動作都是從辭海裡面對「小」的解釋所發展出來的手語,每個舞者學一個手語的動作,發展成自己的獨舞,然後再組成雙人舞的動作。基本上所有的東西,就是在產出辭海裡對「小」的解釋,不過我那時候不太會操作演出,照理說這個應該寫在節目冊裡面。總之,這個作品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動作,都是從辭海裡的一行字出來的,是個很極簡的作品。那為什麼要做極簡的東西呢?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把舞作講得很複雜、很美,而我只要一行字就好,耍酷!好,我們來看一下《小》。
那個箱子就是現場三個地板⋯⋯還不到三個地板的面積,很小。你看我們髒髒的,太熱了,流汗流到像三溫暖烤箱。後面那個是炭筆,我們穿的是白色衣服,每一場跳的時候會摩擦,身上就有一些圖騰,服裝就會開始變色,所以每一場演完都要再把衣服洗一洗,再油漆一次背景。整個作品就是有點動物的感覺,我現在看覺得蠻rough的,有種粗糙感。
你們看得懂那個手語嗎?有些是象形、有些是會意,反正舞者是從辭海對「小」的十二個解釋去編的,然後我們就一直重複。基本上獨舞的動作是一樣的,只是說另一個人會把動作發展成另一個方式,然後配上不同的音樂。唯一例外的是我那個獨舞,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初我沒有遵守那個規則,我可能就是不喜歡守規則的人。那些雙人、獨舞還有那些群舞,很多都是從手語演變而來的,所以你看到那些很奇怪的動作加在裡面,那也是這支舞的特色,突然就來一個手語還什麼的。
我幾乎已經忘了這件作品,我一邊看一邊笑,覺得那時候很年輕,很多東西編的時候就是很直覺的應變,我現在看我不可能出這種招啊,一定都要從一個民族大義、從一個深度內涵的台新藝術獎的觀念去編動作,我怎麼可能嘟一個嘴巴就代表小呢?這太膚淺了!以前就是很單純,想到什麼就做起

Diane: 我在看這些作品時有一個很喜歡的地方,是文中在一個作品裡使用的音樂是很多樣的,從現代的、古典的、美國的、英國的、台灣的、流行音樂、黑人音樂等等,每個作品都有這個多樣性。我有時會想,一個人怎麼有時間聽這麼多種不同的音樂家和作曲家呢?畢竟他如果要從一個人或一張專輯裡挑一首歌,他一定要聽很多這個人的音樂。
林:因為我想要編舞,最重要的知識就是音樂,我當舞者時每次到歐洲我都會去Fnac,就可以在那邊聽,聽到有用的我就買回去,所以我就蒐集了很多編舞用的音樂,反而是流行音樂我比較少買,流行音樂買了之後聽完就會膩,古典音樂或民俗音樂的CP值比較高。我當了舞者十年,就收集了十年的音樂,後來認識了李世揚,很多事情都交給他做,現在我都太懶,後來舞團比較有錢了,就請作曲者去做。我覺得兩個都各有好處。有時候把不同的音樂風格混在一起,雖然不是那麼完美,但是你可以帶觀眾去不同的世界。但是從一個專業的角度來講,這風格欠統一的問題就是一個遺憾,所以你到底要選那一種?
觀眾:剛你說這件作品是從辭海裡對「小」的解釋而來,但我剛看的時候覺得這並不是那麼完全理性的作品,裡面有好多的情感和關係,所以我蠻想知道,在你發展的過程中,你有沒有看到比較關於人性的情感,或者是說,這個部分是怎麼長出來的?
林:其實那時候編完一個很比爾提.瓊斯的《惡童三部曲》之後,我不知道《小》要怎麼做,我只知道場地很小,所以我買了三塊白地板貼在台北民族舞團的排練場,在大直的一個地下室裡面。我還是知道要做什麼,還是用一些傳統的方法去找動作跟關係,一直到我做了三個月、花了十幾萬之後,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舞者坐在另一個舞者身上,他的額頭滴下一滴汗,我才終於了解我要做什麼。那是擁擠而產生的一個觸感的變化,還有當你太靠近的時候,你不會去「看」,你反而會是用味道,就很像你去菜市場,你不會用眼睛看,你光聞味道就知道它的髒亂。就是這個親密的擁擠,很黏的,我們流汗、摩擦,很黏,是一個動物性的主題,這是在地下室做了三個多月才累積出來的作品方向。之前我們也有做一些獨舞或雙人,只是說它真正的核心跟意涵,是在三個多月發展後才找到的,我們再跑去調整原有的素材。我還是那種總是需要有動作、一個句型,後來才調整的編舞者。
觀眾:那後來有調整音樂嗎?
林:音樂百分之三十是我選的,百分之七十是我找人做的。這個人是我國小同學謝宇書,他的本行是室內設計,謝宇書就是唱客家歌謝宇威的弟弟。因為我也不知道找誰,他在玩音樂,雖然他是玩流行音樂,就想說你幫我做啊,因為他自己從高中開始玩音樂,但他玩音樂不能養活自己嘛,所以他主要是做室內設計。在《情歌》的時候,我也用了他一首流行音樂,但流行音樂我都會叫他把節奏拿掉,做怪一點,拉到比較是劇場用的音樂。當我們知道有些曲子我們再怎麼做也不會超越的話,那我們就會用原曲,像中間筱圓的獨舞,其實是用阿拉伯的民歌,那是我們覺得做不出來的音樂,那我又很喜歡,所以我就用了。其實基本上大部分是做的,只有少部分是現成的。
我編舞的習慣是會有替代音樂,因為我會怕我編出來的舞,每一段質感都一樣,所以我這一段可能用巴哈無伴奏,下一段可能用葡萄牙的法朵(fado)3,下一段可能用江蕙⋯⋯這些音樂也會加強我的結構性。編出來後我就把影片交給作曲者,他們可能有幾個選擇,一個是他會聽我原來的音樂,一個是他們會把音樂拉掉,直接用他們的直覺去做,然後真的撞出問題來了,他再聽聽看原本用的音樂。我在正常的情況下,都會在一個月之前把舞編好,替代音樂也都會弄好,最後一個月就是用來調整創作的音樂,但有的時候就是會不從人願啦⋯⋯
註解
- 比爾提.瓊斯(Bill T. Jones),知名的非裔美國編舞家、導演與舞者,為美國現代舞的代表人物之一。比爾提.瓊斯創作力豐富多元,除了在比爾提.瓊斯舞團擔任主要編舞者,也曾擔任百老匯、外百老匯、歌劇的編舞者與導演,曾多次獲頒素有舞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貝絲獎」,也曾以音樂劇《春醒》一作的編舞奪得東尼獎的最佳編舞。他曾於2007年、2014年率團來台演出,除了林文中之外,台灣舞者劉奕伶也曾是其團員之一。
首演於2007年,於新舞台演出。
法朵(Fado),為葡萄牙怨曲,帶有悲慟的曲調與歌詞,內容通常與航海或貧困的人生有關。
文字整理:吳孟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