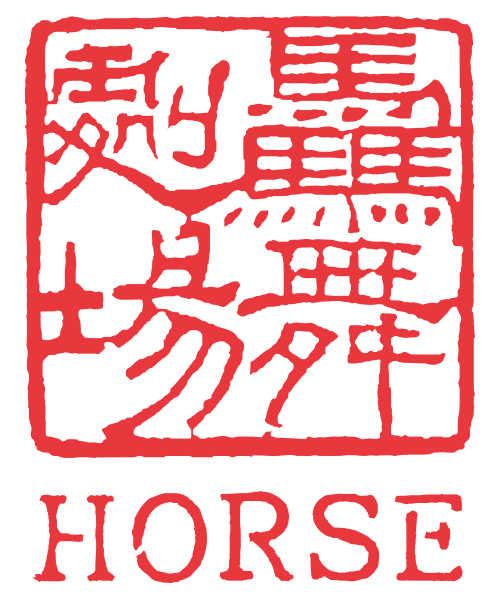「充血:靜坐與演算法也說不清的事」講座記錄

時間|2019.12.06 Fri.,19:00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TCAC (台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1號1樓,近捷運大橋頭站)
講者|王柏偉、孫瑞鴻、陳武康
王柏偉(以下簡稱王):這場表演將在2019年12月28、29日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藝大)表演聽呈現《非常感謝您的參與》,想先請陳武康和孫瑞鴻稍稍透露一下表演的內容與形式。
孫瑞鴻(以下簡稱Ray):我主要從事影像相關的工作與劇場,目前在紐約工作,於2014年認識陳武康,好像可以延伸各自專精的領域,所以開始合作。這次演出是從16年的舞蹈與影像計畫延伸、疊加的作品。
陳武康(以下簡稱陳):我們是從友誼開始的藝術創作,與思考如何公平的交流,在最初沒有想說一定要形成具體的演出。而這次受邀臺藝大表演藝術節邀請,開啟了想要收攏與實踐過去實驗的機會,把我跟孫的關係套用到所有的工作關係裡面。
王:上次在在地實驗分享過的作品(強制對話),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過去合作的形式,與各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處理的部份。
Ray:之前有機會在宜蘭駐村,發展出一個演出形式。當時在形式與規劃上都比較鬆散,可能是他先跳舞、我主要從事拍攝,大概每天花四到五小時左右進行拍攝。對我來說,那種工作狀態是相當平等的,不論是在我的取材或是他的即興上都沒有互相干涉。這些擷取的素材透過各種觀察,去找到素材中的邏輯語彙,演變成最後的呈現。
王:不管在之前有沒有意識到攝影機或是鏡頭,各自在影像裡面有發現什麼原來沒有預期的事情嗎?
陳:我們不想要使用以往的工作模式,就是要不你幫我、或是我幫你的狀態,用肉體去輔助導演的想法、成為他的概念表達,或是他純粹是做紀錄的工作。但對我們來說,是想要用公平的方式對待彼此,在彼此牽制與自由中間取得平衡。過程中不太會去討論我們即興出什麼,或是他要擷取什麼,我們各自在自己的編輯與編舞中發展自己的想法。
王:在舞台上影像的鏡頭是如何移動的,還有攝影機的位置在哪裡?
Ray:大部分是用對稱、或是說包夾的方式拍攝,通常是用兩機進行,在位置與距離上不同。設定上通常會是一個快的、一個慢的,或是說從前面/後面、左邊/右邊拍攝,感覺在這種取材上可以打開一些東西。
王:在這些影像素材進來以後,你要如何處理影像與動作間的連續、不連續性,你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去使用它們?
Ray:感覺要取決於你要做什麼,不論是編輯、拍攝、後置,這整個工作過程在其中體現。當然裡面會有很多步驟,有腳本、椅子應該放置在哪裡、光線要怎麼拍,但這些步驟都是為了要達到我想要的東西。對他來說是一種幻想的目的,好像也不見得會說一定要怎麼呈現。就像是今天拿一塊豬肉,可以切片、切塊,要煎或是炸都可以。
王:那我們看一下影片或許會比較好去想像。上次我看過幾次這個影片,一直有些問題想問,就是這個畢竟是已經後製過的作品,你看到這影片自己感覺到了什麼,如果將它對比你當初的表演,你覺得這還是一個表演嗎?仍然可以是劇場嗎?
陳:這跟正常的演出差很多,在演出時自己會比較忽略旁的人,當有目光在你身上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能量。每次表演都會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會覺得很噁心,但第二階段,比如說中年以後看到就會覺得還好。
王:你覺得在孫瑞鴻的影像裡面,除了自己的影像以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陳:我覺得在看素材跟剪輯之後感覺不太一樣,就會想說原來他是用這種影像的觀點來看,在回顧細節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完整。
王:你們後續想要發展的概念或是狀態是什麼?
Ray:我覺得之前那種工作方式是蠻好的,所以想要繼續往前走。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很多未知的成分,在實踐上有蠻多收穫的,所以不想要只侷限在平面的影像上,而是在現場延伸這件事。
陳:你如果有仔細看的話,每個小片段都會持續三到五分鐘,每個段落都會有一種經過剪輯的獨特語法,之前看過以後就會發現有即興的可能性。就我在表演時,能夠透過這些語法重新互動,在套入影像裡面的我、或是沒有我,在影像時序上、遠近與快慢的決定,跟我重新對話。在這種基礎下,每個設計都會像我們一樣,把自己的成分當作一個媒體與其他人互相交流。
王:這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樣,畢竟這還是影像作品。在現場表演,你要如何去處理影像出現的面,以及攝影機的位置,在空間裡面是如何被安排的,在空間與影像的邏輯上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Ray:我覺得現場的狀況,應該會根據之前的影像做延伸,在舞台上會有兩個銀幕,兩台攝影機會在舞台上移動。之前我們在排練的時候就有試過不同的排法,嘗試在現場直接排練、剪輯,看能不能產生那種現場的「靈光」。
王:我自己蠻好奇現場是不會有位置圖嗎?
陳:那全部都是即興的,當然不會有位置圖,就是可以重複性的東西練一百次,如果要即興的話是不是就要排練更多次?
王:例如像舞台上的大型螢幕是會動的嗎?
陳:不一定啊,螢幕可能也會不見。
王:要不要不見,或是銀幕要在哪裡,誰要推動投影機或攝影機,這部分可以透露嗎?
Ray:全場只有我們,除了我們兩位之外,還有舞台、燈光、音樂以及舞台監督,就在我們六個人以內產出這件作品,透過我們的勞動去產生現場這些東西。
王:那你們會記錄這個表演嗎?是以一機的方式進行嗎?
孫:應該會是觀眾席,以鏡框的方式紀錄。
陳:還是以傳統劇場鏡框式的表演紀錄,看觀眾位置在哪、表演者在哪,然後我擴大到其他的部門。就可能就會有人問說:你的表演性在哪裡?你的舞台、工作可以作為表演嗎?然後售票再分配上會有多少到我手上,到舞台監督手上,觀眾可能會好奇說你今天Cue點做得很好。
王:表演跟Camera的互動,一般來說影像都會被視為結果。那今天攝影機在舞台上互動,這種因果關係同時在舞台上表演,你怎麼讓鏡頭跟影像彼此互動?
Ray:這個關係應該是各自成立的,但在看的時候你還是會分開來看他們,這還是一種觀點,攝影機就是電子的眼睛,我們可以選擇開啟或關閉。
王:我們知道銀幕至少會有兩個嘛?那攝影機呢?
Ray:會有四台。
王:就是在表演者看起來大概是六位,然後有四台攝影機,其中一個人是舞者,是其他人都會在台上嗎?我會好奇,武康如何去思考大家在舞台上彼此互動的關係,就是以舞蹈、身體作為主要的媒介,跟著機器或物件在運動的,在你們這邊的特殊性是什麼?
陳:就是舞監跟舞台脫不開嘛。但除了我自己跟身體的媒體拆不開以外,其他人都可以脫開。
王:從剛才我就有一個好奇的點,兩個從彼此工作的關係,看起來在一個製作當中,往往不會被意識到的平等關係,這對大部分制式的表演來說,不會是太大的問題,為什麼這件事圍繞在表演上會變得如此重要?
Ray:我覺得說,這必須回歸到六個劇場的工作者,大家都有自己擅長的媒材,以職業來操作這件事,會陷入某一種模式,就是有一個劇本出來,大家加起來就會變成這樣的套路。所以我們就會想要去質疑這個被高度規格化、條列化的工作方式,如果把這個問題變成主體的話,會變成什麼?我也不敢說我們一定知道會如何。
陳:就覺得在做主要的發想人、或是編舞的工作上,設計大部分都在後期發展才加入,這會剝奪他們創作的可能性,對我來說是不太公平的。因此要從原爆點開始發展。最後因為製作成本的關係,燈光就會在最後加入。所以我們想要把原爆點在一開始就加入,在有主題演出之前,就能夠了解彼此的部門,產生不聚焦的交流活動。
王:目前為止你們主揪以外的工作,在時間上的安排是如何?
陳:我們會對要在台上表演的時候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不習慣舞台,究竟在上面自己要演自己的身份?還是什麼?
王:畢竟舞者就習慣以舞者的方式在舞台上,但其他人的角色在工作環境中已經被界定好了,當他們站上台以後,除了他們的角色以外,還有他們自己這個身份,就他們還需要拿什麼東西出來。當他們要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是不是需要事先準備特定的東西拿到舞台上,那沒有的話要怎麼辦,就是原來有時間準備、後來變成沒有時間籌備,在資源上要如何轉換。
陳:我們在想說要以租借代替購買,因為很多東西都很花錢,演出完就要丟掉很浪費。我們就在想說是我們需要,還是他們需要我們,就透過這種方式去觀看世界,
王:準備承擔風險嗎?
陳:盡量以不要做新東西為出發點,我允許他們去借其他地方的東西。
王:那在前期排練的運作當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陳:這變成事後討論變得很重要,說大家就在想,作為舞台設計在台上放什麼東西,會改變這個狀態,或是用什麼樣的媒材會產生什麼樣時間的轉變。
王:他們要怎麼樣思考在舞台上要處理的東西?
陳:小柯(柯智豪)他從以前就常常上台,所以他覺得沒差。比如說他就從後台拿一張桌子,以前拿來拜地基主的東西,他覺得聲音很好聽,就拿來當樂器。
王:燈光呢?
陳:對他來說應該更難,因為做設計的就很容易會習慣去跟東西,把他從設計的枷鎖裡解放的時候,他就會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產生一些新的東西。目前覺得最難的是舞監這個角色,他要如何去決定這個跟他有沒有關,他要如何相信這個製作他會是第一人稱。我們也想說,在七八百年前在做這個職業的時候,會是什麼?
王:那 Ray 要不要分享一下自己做影像設計時的難處?
Ray:還好,就是說都很難,所以都很難得時候就會覺得都一樣跨不過去,就是要打開心胸。
王:就是說在這個結構當中,最主要的設定。
陳: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設定第一作者,我們要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他就會覺得比較自在,不會卡關卡在某個地方。
Ray:因為之前有發展其它素材,可以從那個架構去發展,對我來說滿舒服的,就不會變成是困擾。
王:那事後你還會剪一個可以觀看的版本嗎?像是在電影院那樣觀看。
Ray:我覺得表演完就表演完了,應該不會有那個版本,就是現場表演完就沒了,只是會做一個紀錄。
王:那銀幕大概會多大?
Ray:大概有五米,銀幕應該會有兩個。
王:那影像的尺幅會比表演者大很多,你會想要打到滿嗎?
Ray:其實以表演廳的規格來說,已經滿小的了,盡量讓他接近表演者的尺寸。我們希望他是像是視窗的狀態,像是生活裡面的視窗。
觀眾A:我想問如果這個表演的名字《非常感謝您的參與》,您是指六位工作者,還是包含觀眾在其中?就是名稱這樣說,好像會邀請觀眾去觀看表演的感覺,為什麼還會是鏡框式的舞台?你們剛剛說鏡頭都會對稱的,那表演裡面還是會六個對稱的鏡頭嗎,像剛剛播放的影片?你離開正中間的時候,鏡頭是會照到鏡頭的,你在後期剪輯為什麼會想把他放進去?
Ray:一開始我們想到的名字是英文 「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然後放在 google翻譯覺得好像還不錯。現在我們看到表演後面都會有節目單,然後會有意見回饋最後就會說謝謝您的參與,但好像又不代表什麼,有一種很冷的感覺。在這句話裡面創造的關係很特別,身為一個觀眾去看表演也是我們在思考的,雖然是鏡框式的演出是受限於空間的關係,但我覺得這整個表演過程都是表演。
王:如果說觀眾被考慮進來,鏡框式的舞台為什麼還是被維持的?
Ray:那還是一種傳統的觀看關係。
觀眾A:可是你們不是要反抗傳統這件事,為什麼還是會用鏡框?
Ray:或許就是要擁抱才能去推翻。
陳:我覺得這是建立在Code上面。如果說用沉浸式劇場來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們沒有想要變成沉浸式或是把觀眾放在舞台上。
觀眾A:就是說還是要透過傳統的舞台來觀看這件事嗎?
陳:就是說我們還是要在原來的舞台上,用自己的身份去表達這件事情。
觀眾A:如果所有工作者都是表演者的話,燈控的位置在哪裡?
Ray:在舞台上,就每個人的工作桌都會在舞台上。
觀眾A:都在舞台上是說會特別空出一個空間給他們嗎?
Ray:關於攝影機這件事完全不在意,就是他就存在在那裡,並不會說要刻意去剪掉、不讓觀眾看到。對我來說規劃了這種方式,就是攝影機一定會看到對面的機器,他們的存在是必然的。
王:我想舉另一個例子,來贊同這個疑惑。大部分的VR影像必須把下面自己出現的點修掉,才不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沒有頭的影像,這個影像就會變得很怪,而必須去把暴露出來的部分修掉。他的問題是說,在影像上反身性看到攝影機很像是有點怪的事情,這在你這反而好像沒差。
Ray:這是某種目的性去創造出來的質感,所以說好像不需要刻意去把他修掉。他所有的東西都是裸的、沒有修飾,這些編輯跟剪輯的語彙都是從素材中找到的,然後你從素材裡面去尋找連結的點,讓他們連成一個關聯的東西。
觀眾B:第一個剛剛說這是即興的演出,燈光、音樂設計、舞監等等,他們在即興的時候要如何溝通,溝通會變成很有趣的事情,是說這個音樂變慢、你就要馬上變慢嗎?就是說你們在創作的過程是用這種做法,然後從過去的嘗試中找到有趣的方式,如果是這樣的話還算是即興嗎?這些部門要如何影響創作。
陳:這個即興與未知,其實並不是一種完全不知道的狀態,我覺得這跟佛教有點關係,像是 John Cage做到最後也是接受自己的問題,當他光打到那邊,我到底要不要接受、或是拒絕,觀眾可以看到我要不要跟著光移動,讓他的光打出我的背影,都會變成一個可見的問題。觀眾就可以站在比較遠的位置去看,看到這其中的權力關係。有時候就突然打出個燈光,嚇你一下之類的。
Ray:我們音樂設計聽到就很興奮,爵士就是即興的最好的例子。他們有100首即興的歌都必須要練,在 Jam的時候就變成誰要接誰,你要變的時候他要不要接?這過程就會變得活靈活現,然後去內化他們。
陳: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們也不能反悔,就是知道說他會有這兩個選項,我在現場只能選一個,這件事在舞台上是會被發現的。因為表演者把所有決定都放在最當下,這是我覺得唯一能做的,所謂劇場的當下性被體現的過程,這很難跟電影或其他東西做區別。我們很多的對手很難賣票,我們都很習慣平面的習慣,所以你會用這種習慣去看劇場,也會用這種思考去看作品、去思考創作。我覺得這種狀態下現場就消失不見了,所以我們要重新去思考什麼是現場演出,將他提煉出來。
王:我很好奇你們從現在到表演那天,前面安排了幾次排練?
陳:就是每天,從禮拜一開始。
王:你們剛剛在講即興的時候,大家都在事前有深厚的功力,在什麼樣的選擇下不會崩掉、壞掉,這個可能性在高手與高手之間對練的時候,是很容易接招的、而且好看。但如果沒有的話,就很容易崩解掉。這跟完全不要有接觸的即興狀態其實是不一樣的?
陳:很多舞者對於音樂或舞台都是很熟悉的,雖然偶爾還是會有耳包的情形,但還是有一定的敏感度。這次影像和我的關係就不太ㄧ樣,什麼時候發現他的變化,然後再依據他的變化做改變,或是舞台設計放了一張椅子我到底要不要坐的問題,就不管怎麼樣都要決一死戰,有時候你也會看到表演者死都要撐到結束。話說回來,還是取決於我們為什麼要去看這個現場演出。在看 Trailer的時候好像就會期待影片的印證,有時候就會不想去看,就像電影。可是這個現場就會有比如說空間、抉擇的變化。
王:我想請問Ray跟武康不論是在影像、投影的形式操作上,你覺得自已在上面的想法有什麼改變嗎?或是有產生新的操作方向。
Ray:一定有改變,如果要量化的說的話,就很難表達。就是它是一個人嘛。因為拍攝了很多,過去我自己不太會去拍人、物品什麼的。
王:你會把這樣的拍攝方式反饋到比較靜態或是物件的方式,在裝置或是物件上會反映嗎?
Ray:可能說同時間多焦點吧,如果在同時間看到很多的角度,用這種方式觀看的話會是什麼東西。
王:就是你會不斷地切換單頻或雙頻,跟你說的同時間多焦點會有關係嗎?就是同螢幕呈現不同的觀點之類的?
Ray:現在有什麼,就會用這個狀態去反饋他,就看他現在是什麼情況,而我去用什麼方式拍攝。
王:就說這兩個投影幕是當下決定的嗎?
孫:就是我直覺覺得不會是一個、也不會是三個,或是四個。
王:這個邏輯可以說服我,就是比較不會是電影式的,三個又很像鏡框舞台。就是本來說有四個選項嗎?
陳:但他就不會是一個鏡框。
王:就是說這樣就不會是一個鏡框舞台的形式,會破壞跟觀眾的關係。
觀眾C:我很喜歡看即興、混沌聲響混沌身響 第四季,就是你們的宣傳就是很混沌未明、很吸引人,就是說看到宣傳影片就能想像到全貌。舞者跟音樂家的即興,再來說燈光合作很久也有一些即興的成分。這次就有銀幕進來變成即興的成分,成為新的元素,但舞監就不知道會有什麼可能性,像現在很多表演,但就是看不到創新的成分。剛剛觀眾問的,混沌聲響他們完全沒有見面,中間有些崩潰的成分,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排練;而這個即興有很多排練、很多練習,大家都誤會了即興這件事就是完全沒有練習,而你們裡面就是有不斷了練習、排練,卻不要去把他安定下來,這種不斷的 Score,會有像是大綱的東西。雖然說我到時候去看會看到那種已經很純熟的關係,他們已經知道做這個選擇會產生什麼效果。這次我聽到現在,這種不斷排練的過程激發的火花,會讓我想要看到現場的狀態,可能兩天看到的東西都會不太ㄧ樣。就是你們排練到現在,應該會有大的骨架出來。
Ray:即興對一般觀眾來說,不一定可以馬上懂、看到點,很多時候再看即興會有茫掉,因為資訊量太大。這次我們不是想要做得很複雜,希望可以讓觀眾清楚的看到這些事情。
王:我有點好奇反向的狀況會不會發生,在足夠的排練習慣以後,會有定型的問題嗎?你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鬆動這個狀態。
孫:我們其實還沒開始排練,所以還不會遇到。
王:像我作為藝評如果比較懶惰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定型的狀態,等於說在固定的架構裡做一點調度就好了。
陳:我們還沒定,所以還在一直丟東西,還處在很興奮的狀態中,還沒到做決定的時刻。
王:這次的部門比較多,你們會讓他們稍微錯開的時候嗎?
陳:就是大家都在動的時候,大家都會跑來找我,所以我們會想要去避免這種狀態。
王:所以還是會避免去這種傳統的,以主角為主體的模式。
觀眾B:我們在說電影、繪畫、話劇都是根據你們想像的狀態去創作出來的,武康一直強調這種公平的創作,最後還是呈現出了作品嘛,百分八十都你們的心血,感覺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即興的。
陳: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我們只能開時間跟空間給大家。具體會變成怎麼樣會是大家決定的,只是因為我們兩個是主要作者,所以在比例上會比較高。如果舞台設計去抓了一把沙,說舞台就像樣沙一樣流逝,我也不能說什麼啊?但很多形而上的討論,是我們排練過程中的階段覺得很有趣的事情,然後討論說誰會是第一個人,假設以一個劇場來說,誰會是最大的。以個人來說,我們會說舞監是最大的,他如果說要放一顆燈,我就會說燈不是你的,他就說他不管,因為在舞台上他最大。當我在跟設計工作的時候,就會問他說你在做什麼樣的作品的時候,你會覺得作品是你的,而不是舞台的。就是說主揪、設計,就說主揪通常到最後就會發現自己最少錢,然後就會很納悶最後怎麼會變成這樣。
王:我滿好奇你們形上的討論,就是這個討論的部分可以多透露一些嗎?在觀眾看到作品的時候能夠多穿透這個部分。
陳:就像我們同時在看這個題目的時候,想到的就不太一樣。我們拿到問卷,看到最後一行的字,就會想說因為對方在,所以自己才存在,因為要有人觀看才會有意義,就會很感恩。就說如果再開設計會議,就會開完會然後回去做自己的事,這次在討論裡面就會知道說原來設計他的背景那樣,所以會做出那樣的東西,這個美就是屬於他的。
Ray:每個人參與的個性非常突顯出來,這是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會看到的,好比說廖音喬他就比較喜歡直接,每次進來就放、丟東西。如果是徐子涵就會從外面,另外一個就會偶爾來一下,沒有想到說大家素材量減到底的時候,本人的質地就會在舞台中出現。柯智豪就說這就是⋯⋯貧窮劇場。
觀眾D:你剛剛講到漆油漆你會不知道他在幹嘛,就是說每個人來帶的東西都會不一樣對嗎?傳統劇場都會有劇本或脈絡可以去解讀,就在你們舞台上每個觀眾都可以有自已解讀的方式,你們會去問彼此在當時做某個動作的想法嗎?還是說就是過了就過了?
Ray:會。
陳:就是說如果是鈔票、表達議題,可能還可以。
孫:或是說拿一袋膠囊?
陳:就說他如果拿膠囊就會有符號、有情節,這個就會在後續進行討論,如果只是很直覺的話就會享受那個過程。我在跟他對話的話,如果有觀眾在看我跟影像互相影響的話,音樂如果出來加進來,你在聽感上就會被他詮釋了,或是燈光進來的話,你就會跟著他去解讀。
孫:會嘗試。
陳:我不會想要理解,我覺得這是當下發生的事情,反而會去檢討那些比較實際的面相。
觀眾D:比如說膠囊或油漆?
觀眾B:所以你會憑你的直覺去反應?
觀眾D:如果他覺得他很了解你,所以要給你那些東西,你會檢討嗎?
陳:就是他覺得他想要給我這個東西,可是我都不想跟他,他可能會覺得很受傷。
觀眾D:所以三週後你們就會很了解彼此,也不需要溝通了。
陳:我覺得到最後就會變成接受的狀態,不見得說要變成什麼狀態才能被詮釋。
王:在這邊我最為觀眾最大的疑惑,就是你們工作過一陣子,你們能夠理解到什麼階段是在理解、詮釋或發生,或是超過這個界線。但對觀眾來說他們並不會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對我這種觀眾來說,這次看到的部分是理解、資訊或是發生的部分,變成被迫不得不接受。你們在過程中都需要去檢討,對觀眾來說也想要去辨識哪些部分是偶然的發生,還可以繼續探索、推進結構的部分,是在一種選擇的狀態下做的決定。
陳:這應該是在演後座談討論的部分,說不定在演後你就覺得不需要了。
王:我覺得每次即興的演後座談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陳:對我來說根本不需要即興,因為如果很好我就會很享受那個狀態,如果很糟你就只會想要早點離開而已。對我來說裡面有公平啊、理解與觀眾的關係,這些希望都能在作品裡面呈現,但即興的部分或許根本沒有辦法討論,因為會有很多偶然的成分。
觀眾E:當不是舞者的人站上舞台,在鏡框式的框裡面,那些不是以舞蹈為主的人,他們的動作也會被納入表演中嗎?他們用其他媒介去表演,會包含他們的身體嗎?
陳:就是他在cue燈的時候應該不會有刻意的身體表現,但他們就還是在做他們正常的事。目前我自己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沒有本,像國王的新衣一樣,就是真的沒有衣服很赤裸的感覺,就說如果沒有文本的話就真的不能對話嗎?就在享受這種素材跟素材之間的對話。平常在看演出的時候,就會忘記有燈光,因為他們全部都被放在一起了。
文字整理|陳韋綸
編輯|莊博舜